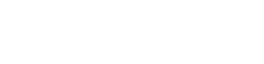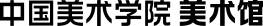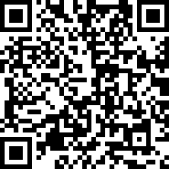展览信息
展览 /
完美之路——杭州,马可·波罗的“天堂之城”
时间 /
2024.11.10-2025.1.10
地点 /
南山路218号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主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
威尼斯双年展
承办单位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威尼斯双年展当代艺术历史档案馆(ASAC)
特别支持
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
意大利驻沪总领事馆文化处
策展人
路易吉娅·洛纳尔德利

奇迹寻踪
八小时片长(原片为九小时,根据美术馆开放时间剪辑为八小时版本)的电影《奇迹寻踪》(In Course of the Miraculous)建基于几个真实的历史事件,由三个合共横跨一个世纪的故事交织,组成一个平行发展的叙述,讲述在攀喜马拉雅山、跨越大西洋以及远洋捕鱼的过程中发生的故事。

程然
生于内蒙古,现工作和生活于杭州。
2013-2014荷兰Rijksakademie 皇家视觉艺术学院驻留,2017年创办艺术家空间Martin Goya Business.
作为中国新一代影像和跨媒介艺术家的代表,程然尝试电影,诗歌,戏剧,小说,装置等不同艺术形式,但并不拘于某种专用材料的使用,跳跃的,抽离的,更具实验探索的精神,在作品中他改变了原有物质的空间,结构与感知。程然在文本和视觉语言之间的转换让观者游离于真实与想象之间,呈现了某种虚空的诗意。他将这些审美元素重新组织形成自己的独特的艺术语言。这些作品都反映了在政治与文化全球化冲击下中国年轻一代内在的生存状态,程然不再关注所谓的身份认同问题,而是更多地从多元文化中发现新的价值,看起来艺术家自我的判断被隐去,但这恰恰是艺术家在创作上自主性的体现。也因此,程然从各个方面体现出他对于边界、差异、甚至对抗、边缘化等主题的思考。
Q1
请您介绍一下此次参展的作品和作品所涉及的三个历史事件。
程然:这次参加展览的作品叫作《奇迹寻踪》,拍摄于2014年,里面包含了三个关于失踪的真实故事。第一个故事发生在19世纪初,英国的探险家乔治·马洛里和他的同伴一起去攀登喜马拉雅山;第二个故事关于一个荷兰的艺术家Bas Jan Ader,他人生中进行了众多的行为艺术表演,最后一次表演发生在洛杉矶,他希望用一艘小的帆船去横渡大西洋;第三个故事发生在2010年左右的中国,是鲁荣渔2682号出海打鱼的故事。三个故事都是关于失踪或者探险的。
Q2
我们了解到这三个事件都是有关未知,且充满不确定性的,那么您为什么选择这三个历史事件?有什么特别的考量?
程然:首先,这三个历史事件他们跨越了100年左右的时间,它们发生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是包括了不同历史的故事。我认为关于探索始终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所以也许通过这样的一个跨越时空的故事,我们可以在一个影像中去探索什么是冒险或者什么是幻想。

Q3
电影的拍摄过程中您有哪些印象深刻的事?
程然:这部电影非常不一样,它筹备的时间跨度是非常长的,从2013年开始到2014年拍摄完成。在拍摄的过程中,我把这个电影当作一个艺术项目,我们把它分成了很多组不同的展览和演出,不断地在复现,比如它的剧本,它的音乐,它的最终成片……直到现在它仍然在不断的变化。包括这次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做展览的方式,也是经过调整的。
我觉得《奇迹寻踪》这部电影,它带给我最深的感受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影像,在跨越时间的长度里面不断的去探索自我,去应对它所面临的挑战,在每一次展览和每一次演出里面,它们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去呈现。所以从这个层面上,《奇迹寻踪》就是一个与奇迹同行的片子,可以列举出非常多有趣的事情。比如这部电影有一个40分钟长的片尾曲,可能对于很多电影而言,这是没有办法去实现的;再比如我们按照非常古典的电影的方式去设置的4个中场休息的时间,这是在百年前电影刚刚出现的时候经常会使用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实验影像或者说艺术影像中,我们可以用到传统的模式同样去达到一个对奇迹的探索。

Q4
《奇迹寻踪》长达9个小时,您为什么选择挑战制作如此片长的电影?
程然:从2003年到现在,我拍了有上百个短的影像,影像作品对我来说一直是非常重要的创作媒介,或者说是唯一的创作媒介。因为杭州是一个影像艺术、新媒体艺术生态非常强的的城市,我也深受很多本地学院的艺术家朋友的影响,我觉得影像是一个与生俱来的媒介,它是充满先锋性和挑战性的,所以从一开始我就会选择影像作为自己的创作方式。
但我自己也会去想,当你拍了很多短的影像之后,到底还可以用这种媒介去挑战什么——时间也许是一个重要的切入点。所以我就选择去拍这个可能会长达9小时的电影,为什么是9小时?
我觉得它有几种标准,商业电影是在一个半小时左右的长度,好莱坞电影是可能在两个半小时左右,但世界上仍然有一种影像,是它超越了7小时的,可能在7小时到9小时之间。我有非常多的偶像,他们也以这样的时间长度去创作,这对我而言是一种激励,或者说是指向。比如说贝拉·塔尔的《撒旦的探戈》、法斯宾德的《柏林亚历山大广场》、王兵的《铁西区》……所以我觉得影像的长度它不仅仅是代表时间的,我觉得更代表一个艺术家的态度或者一种行动的标准。同时9小时在很多情况下也是一个工作的时间,或者说是一个机构的开放时间,甚至是超过某些机构开放的时间的,比如这次展览其实我们把它压缩到8个小时。时间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们是否愿意用一天的时间去幻想或者是进入到一个艺术的氛围里面?我可以通过这个影像去分享很多在时间之外的想法,每个观众也都会有不同的想法从“虚度”时间中产生,这便是影像的时间带给观众的意义。

Q5
超长的片长带来了哪些困难?
程然:它带来的困难是远远比想象中要大的,因为它不仅代表着工作量的翻倍,它在更大的层面上是代表着某一种结构性的规则没有了,你没有办法再去依照一种既有的规则和模式去创作,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自由。当你超越了一个时间的框架和一些规则的框架之后,你所做的一切可能都是非常自由的,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去束缚住。所以在某种程度上里面所面临的最大的困难就是自由。当你面对一个没有规则和没有经验范畴下的自由时,其实是非常难把控的。
除此之外也有非常多的实际性的问题。比如说我们需要一个9个小时的剧本,那么谁可以去写这个剧本?我们还需要邀请音乐人去配乐,那么谁的音乐可以去达到几十分钟的长度?谁的音乐可以在电影里去呈现出和视觉、时间并行的声音?因为并不是所有的艺术家和合作者都可以理解以这样的方式去创作影片,这些都面临着非常大的问题。最终我们找到了非常好的编剧路易斯·诺,非常好的配乐团队惘闻乐队去参与制作。在某种程度上,《奇迹寻踪》是在寻找同频共振者,这个可能是9小时的片长所带来的时间之外的一些东西。


Q6
请问《奇迹寻踪》与惘闻乐队的合作是如何展开进行的?我们了解到这些作品的配乐是通过跨界实验的形式完成的,请问您对合作的初衷是怎样的?
程然:2014年惘闻乐队与《奇迹寻踪》的合作是我们的第一次合作,直到现在,我们仍然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合作。首先我认为惘闻乐队作为后摇乐队,他们是没有歌词的,然后他们有非常多的成员,能以非常复杂的编排形式去创作自己的音乐,而且据我所知,他们到今年为止是一个具有25年历史的乐队。惘闻乐队的音乐本身就是艺术的一部分。我非常荣幸能和他们一起工作。
在当时的拍摄时,我们的合作也是一拍即合的。当他们得知一个艺术家想要去拍一个9小时的电影时,他们首先的感受是非常兴奋。无论从视觉还是声音的角度来说,都会给创作带来非常大的难度。
我们讨论怎么样去开展工作,实际上最后的结果非常简单,当我们选择在北京的一个影棚中去完成最后一次拍摄的时候,我们邀请了惘闻乐队去到我们营造的一个400平米的黑色的海面场景里去做了一场演出,这场演出是一场长达40分钟的即兴音乐实验,它同时也是影像的片尾曲。他们总共为这件影像作品创作了超过3个小时的声音和音乐,我觉得对我和对惘闻而言,这都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遗偈博物馆
《遗偈博物馆》是陈量自2016年以来对于书法史中一种特殊的书写现象——遗偈的持续思考。“偈”是梵语中“颂”的音译,在佛教中,高僧临终时所留下的偈叫做“遗偈”,通常用来表达对于佛法的理解或临终的感悟。遗偈是生命极限之处的书写。
遗偈一方面作为绝笔之书,昭告世人“我”的存在,并期待被感召而复活;另一方面,它又是“我”的绝境。在这样的生命仪式中,书写与诗文在濒临绝境下获得余存的精神力量。遗偈作为一种特殊的书写现象,包含着书写精神与生命感悟之间崇高的关联,它更是一种“否定书法的书法”。
《遗偈博物馆》由三个部分组成:影像《石鼻正受》,三十四件遗偈诗文书法立轴,以及一个霓虹灯装置。其中,影像作品《石鼻正受》是以不今不古的表演方式,重新演绎唐宋以来的诗人书写“临终诗”的仪式传统。以“石鼻正受”为名,阐释诗人、师友感情及其周遭自然万象之间的生命关联,整体展现出“书写遗偈”的仪式过程和自然象征。立轴作品遴选唐宋以来三十多篇遗偈进行书写和重新演绎,将此仪式过程与书写痕迹置于博物馆的展览叙事模式下。依此探讨书写与生命感知、绝笔诗的历史、书法的物质性以及现代博物馆制度诸问题。
艺术家

陈量
1987 年生于陕西宝鸡,现生活、工作于杭州。幼时跟随村里画庙师傅学习书法和神像绘制,成年后在陕西科技大学学习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专业,后于中央美术学院实验艺术学院和中国美术学院书法学院就读,并获得博士学位。自2012年成为职业艺术家以来,他的创作和研究基于对地方知识的田野考察、古代仪式、文字起源和人类书写的传统,并始终朝着挖掘被隐藏的历史和书写普遍性的状态前进。由于受到民间仪式、神秘主义和长青哲学的启发,常使他思考如何将零碎、混杂的民间思想以书写的方式重建。这使其工作包括以图像学和文献收集、出版、田野、纪录片、写作、诗歌、剧场、书法和绘画等各种方式展开构建了其复杂的诗意视野。他还对理论研究、民间亚文化、艺术乡建、以及地方传说和信仰充满热情,并于 2020 年创立仪式民众剧团(CPT)。他的工作执着于挖掘、重新发现和解释呈现那些曾经迷失、未闻和被掩埋的痕迹和声音。
Q1
请您介绍一下此次参展的作品。
陈量:这件作品是从2016年到今天一直在做的一个项目,叫“遗偈博物馆”。最早是在16年的时候,我在网上发现了诗人海子写的遗嘱,在遗嘱里边他描述了一系列非常迷幻的事情,说别人在发功害他。他遗嘱中的语言里有一种特别的书写力量,给我一种超然的感受,这种感受促使我想要系统研究一下有没有这样一种专门的研究,即人在临终时的写作或者书写状况。
后来我发现在禅宗里有专门的一种仪式,叫请偈仪式,指的是师傅在临终的时候,他的学生或弟子会发觉他的弥留状况,便请求师傅写下临终遗偈的仪式,这种仪式大量出现在禅宗的公案和史料里,比如像《五灯会元》。
当我系统阅读和研究了遗偈语言和遗偈墨迹之后,便思考人在最后的书写状态。因为我本身是研究书法的,又一直在做书法的创作,对人在不同情境下书写的语言、书写的节奏,书写行为本身和生命交织互动的情感,这些层面非常感兴趣。
所以此事对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一直到今天这个项目也没有做完,此次展览只展示了其中的一小部分。作品整体大概会持续到2026年完成,会包括一本名为《遗偈研究》的著作,200件遗偈作品,还有相关的文献等等。

Q2
此前有观众在参观《遗偈博物馆》时感慨说创作时要感受这种临别的心境,您的创作过程应该是内耗的过程,您是否同意她的猜测?那在书写的过程中,您的情绪和心情经历了哪些变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陈量:观众能从我的书写里看出内耗或者情感的孤绝,我觉得是非常欣慰的。这里展示了33件作品,我曾预设我在写每一件作品的时候,都经历了他们的一生,像演电影一样。每一位遗偈的作者在书写临终之笔的时候,都要写下其一生的总结,所以我不能轻易地把这个句子简单地抄下来,直接挂上去展示,而是我必须要进入他的那个生命阶段中。
我的工作包括这么几项,首先去理解他一生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当然史料是有限的,我从各个方面来找他的资料,包括他留下来的相关书法墨迹,从他的墨迹中看到他书写的习惯、书写的风格,再来研究他的诗歌文风,因为所有的遗偈都是以诗歌或者偈子的方式书写下来的。
所以最终我得进入他的偈颂情境中来进行书写,实际上是试图让我自己进入了他的身体,进入了他的生命阶段。用他的生命方式来书写这件事情,这是我试图去做的。


Q3
幼年时接受了乡村艺术教育、本科读的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过去的经历对您的作品有什么帮助和影响?
陈量:我学习艺术和书法的过程,可能跟大多数美院同学不太一样,我的第一口奶是在村中的庙里学的,所以我的创作和研究一直关心书写跟宗教以及跟人的互动关系。
庙在农村,实际上是一个情感凝聚的中心,书法、壁画、建筑包括雕塑,这种总体性艺术呈现在这个中心里。在这种观念下,书法实际上在地方世界里起到一个维系情感、乡村治理的作用,它产生了一种情感互动。但是在精英的世界里,书法可能就是个人的一种消遣或者某种文化表演。
所以我的书法研究和创作一直关注关心书法内在的东西——情感的互动和生命的关联,甚至是书写内部的精神驱力,以及凝聚民众的社会基础,而研究这些必须涉及到书写起源的问题,而书写的起源又在地方的书写仪式中显露无遗,这些都是我非常关心的书法问题。由于我在本科的时候学的是理工科(材料科学与工程),我的工作方法又特别接近实验室里的某些推进原则,像在实验室里做实验一样,把它做成一个项目,结合田野调查的实学基础,不断进行推演、进行优化,直至完成。可能是不同的学习背景,造就了目前作品的研究和呈现方式。

Q4
您曾经提过想要探究中国书法内在的精神驱力到底是什么,您在创作这件作品的过程中,是否有新的推进?
陈量:当然,这个项目实际上是通过书写来表达人和人的群体之间的情感关联和互动,我觉得这是一个至为重要的书法课题。书法若真的有其内在精神,那么这个本质就是人书关系,无论是书如其人、人书俱老还是掷笔而逝的遗偈昭告,皆在言说人和书法关系的紧密度。但是我们发现,今天的书法大多数时候变成一个外在的东西了,比如我们为了表演才能让小朋友去写书法,为了参赛获奖,或者为了申报某个项目,大多数情况下书法成为了一项文化表演,而不是参与者自觉地感知书法、感知它的内在世界,这些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使得书法变成了一种外在的传统,而不是内在的传承。
书法内在的传统是什么?“遗偈博物馆”这个项目实际上促使我去思考,书法有一个非常深厚且特殊的传统——源于人的精神内在的遗偈书写。禅宗将这种书写的行为方式命名为“遗偈”或者“示寂偈”等,实际上这种书写行为及其方式,不光禅宗系统有,民众、道家以及文人都有这样的书写。比如史料中记载的一些行刑犯,他们在被砍头的时候写下绝笔诗,比如在道士在升天的时候,他要写下临终偈,包括历代文人更留下大量的临终诗篇。
不过,唯有在禅宗里,它形成了一个系统的仪式。在我看来,至少在书法史的层面来讲,它是第一次如此直接地将书写跟生命直接联系在一起的书写,这种直接而孤绝地碰撞,甚至使得书法史都变得有力量、有情感。“遗偈博物馆”中的每一件作品,可能就是一个人一生的象征,它是一种昭告。虽然“我”人走了,但是你看到了“我”的墨迹留存了下来,“我”的墨迹在,当你们看到它的时候,相当于“我”还用“我的眼睛”在看着你们,看你们在做什么。遗偈形成了一种昭告,缔造了一个余生。

Q5
有没有哪件作品在临写的过程中让您印象深刻,或者比较困难的,请介绍一下?
陈量:可以说,每一件遗偈都很特殊。如果确实要选一件来讲的话,在面前所有的遗偈里最上面那件元代著名高僧无学祖元的《临刃偈》挺特殊的。这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他在年轻的时候去化缘,在路上碰到了元军,元军要杀掉他,大刀已经放到他的脖子上了,他说杀掉我可以,但是请您再等一会儿,我得先按照禅宗的仪式写下遗偈,然后他就慷慨地写下这首诗。这件作品就在这个位置,应该是这里面最大的一件——“乾坤无地卓孤筇,且喜人空法亦空,珍重大元三尺剑,电光影里斩春风。”那种电光影里斩春风般的决绝,非常迅速,没想到遗偈刚写完,元军就被感化了,没有杀他。
这件遗偈实际上没有实现遗偈的功能,变成了一件不是遗偈的遗偈。但我觉得它又能够代表遗偈最核心的精神,所以把这件作品写下来。书写过程里,我最初也觉得可能用一种普通的书写方式不能表现高僧无学祖元决绝而去的书写状态,所以以速度极快的笔法书写,像大刀一样在斩在纸面上,形成一种遗偈的力量,展现书写和生命交织下孤绝的勇气和彻悟。

Q6
《遗偈博物馆》是否是您比较有突破性的创作?这种突破背后的关注点是什么?或者推动创作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未来有怎么样的创作计划?
陈量:也很难说,因为这个项目是我目前最长期的一个项目,从16年一直到26年,整个创作会有10年之久。我的所有创作都是基于我长期的研究,而不是一个灵感或者一个临时的方案对策。我的工作往往是把我的研究做到一定程度之后,在研究中长出我的创作,基于田野工作推进和生成自己的创作和研究,这是一个互动过程,并非传统的“构思-方案-创作”的简单逻辑。所以与其说这些展示的东西是作品,倒不如说它们是我研究和田野工作的一个手稿或一个过程记录。我其他的作品也是跟民间、地方以及人的情感相关的书写、艺术以及仪式相关。
地方社会中的书写,尤其是仪式中产生的书写有其内在的生命力,这种精神驱力是我的研究和创作探讨的核心。由于仪式是一种广泛存在且能够使人的精神状态产生扭转的这么一种人类行为方式,它通过象征运作使得其中的人、物、语言、动作皆产生“有意味的关联”,比如一个人在现实中受挫,他可以通过仪式得到某种精神性的补偿,仪式的神奇之处就是能让人在其中得到结构性的转变、僭越甚至超脱。所以仪式中的书写自然与传统意义上的书法不太一样,但书法又起源于仪式,所以仪式中的书写更像是文化意义上的书法的原初状态。所以民众的生活中的书写艺术,那种包含情感凝聚力量的书写文化,包括公园里边的地书书法,都是我特别关注的项目。我尤其喜欢看公园里老大爷拿长杆子棉花写字的场景,它有一种温情,这跟精英书法那种高高在上的状况不太一样,它完全是一种生命化的运动,它也更接近某种日常生活的仪式。
所以“遗偈博物馆”中的这些作品也是生命化运动的一个书写缩影,接下来我的作品也会继续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探讨。接下来的几年,我必须要不断地推进关于仪式的研究和考察工作,随着观察的深入可能会出现一些新的方向和目标。它或许包含类似“民艺运动”中的某些观念,甚至包含更为广泛的历史和演变间隙,以及那具有普遍性的、结构性的中国智慧。但它具体是什么,或能带来什么效应,现在很难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