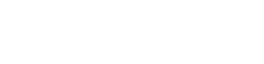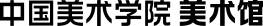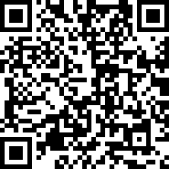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Q&A
/
冯冰伊&唐潮&吴鼎&郑源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实验展厅
在半个迷宫中
艺术家:冯冰伊、唐潮、吴鼎、郑源
策展人:刘畑
2019.12.04-2020.01.03
迷宫最早出现在古希腊神话中,由雅典的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建筑师和雕刻家代达罗斯所设计,用于囚禁半人半牛的怪物弥诺陶洛斯,半人半神的英雄西修斯在迷宫中杀死了怪物并逃出了迷宫。现代社会,当人们抵达一座陌生的城市,就像进入一个未知的迷宫空间,往往要依靠导航系统的帮助才能找到将要前往之处。但在我们生命中所需要面对的那些路径更为复杂且无人导航的“迷宫”中,又该如何找到出口?而深陷其中的我们所看到的真的是整个迷宫吗?或许从未有人得见迷宫的全貌,再广阔的世界也不过是“半个迷宫”。

唐潮,《卧室里的糖》
影像装置,投影、蓝色LED、透明气球,4k,时长不一,2019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图片由作者拍摄

唐潮,《雨点击目光》
单屏影像,4k,3分21秒,2019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图片由作者拍摄
若置身在半个迷宫中,则意味着有更多道路的开放,但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曲折迂回。如果我们以最笨拙的方式沿着一面墙随着它的转折一直行走,应当可以准确地找到出口,并且,它会是无限的出口。也许我们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解读展览“在半个迷宫中”。

吴鼎,《关于圆的历史》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艺术家郑源的作品,像是从已经盖棺定论的结果中重新寻找另外一种可能,比如在影像作品《普罗大众之夜》中,艺术家将婚礼视频的时间轴进行倒转,回到图像所诞生的那一刻。这看似是一个剥丝抽茧的过程,在大量的图像中,除了以婚礼记录为目的而被选择的所谓的“对的”图像之外,是否还有另外的可能,而原本“错的”图像,在揭示了一段潜藏的叙事之外,也提供了一条新的通路。图像在不同的使用企图中,有不同的选择方式,而如今,在每时每刻都产生大量图像的时代,又有多少故事在被编撰,又有多少人,迷失在图像的迷宫之中?

郑源,《普罗大众之夜》
单通道⾼清视频,彩⾊,有声,29分17秒,2019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图片由作者拍摄

郑源,《无事发生》
单通道⾼清视频,彩⾊,有声,5分23秒,2014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郑源,《游戏》
单通道⾼清视频,彩⾊,有声,17分01秒,2017
艺术家唐潮的展览路线并未存在更多的岔路,它一通到底,这会是迷宫中可以让紧绷的神经稍做缓和之处吗?但站在起始处《雨点击目光》作品前,望向幽暗的无法预知的展厅另一端的时候,我彻底打消了这个念头。唐潮所展出的作品均以自身为拍摄对象,在不同的作品中放大不同的感官给自身或身体带来的经验。悠长通道中的十件作品,是艺术家留给观众的碎片式的线索,当这个迷宫的分段进入尾声的时候,观众也许会获得一种在另一个“人”的视线关注下产生的带有温度的回馈。

唐潮,《结晶》截图
单屏影像,4k,6分钟,2019

唐潮,《蝴蝶暗房》
三屏同步影像,4k,11分07秒,2019
艺术家冯冰伊在展览空间中预设了一种观看的路径,绿色的地毯像是迷宫中点燃的火光。而绿色的高饱和度,相较于其他颜色更能形成色差,也更容易追踪物体和定位,这似乎又预示着跟随这条线索,可以抵达迷宫的出口。但事实亦非如此,所有的追寻都伴随着歧路,作品《混合演绎》的转角处,多屏影像作品《SCP项目等级:爱与冲突》像是突然分散的线索,让线路变得不再单一,抵达之后才发现,末路并无出口。作品中随机抓取路人看与被看的镜头被分散地放置在狭小的暗空间中,似乎在回应《混合演绎》微缩又可控的排演场景。而有趣的是,虽是末路但并非死路,这些作品的附近又设有通往室外空间的出口。当我们习惯了影像空间惯常的黑暗之后,眼睛在接收到出口处的强光时,会产生瞬间的眩晕,也许这就是影像的“神圣时刻”,也是这个非单通道迷宫的另外一种答案。

冯冰伊,《从洞穴中来》
双屏幕影像装置,彩色/有声,循环,2019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冯冰伊,《混合演绎》
单通道影像,彩色/无声,5分钟,2019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图片由作者拍摄

冯冰伊,《SCP项目等级:爱与冲突》
多屏幕影像序列,混合媒介,时长不定,2019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整个展厅看似是四个相对独立的展览空间,但却环环相接,并且无论起点在哪里,最终都将会回到艺术家吴鼎的展厅空间。也更好地呼应了他的作品《关于圆的历史》。展厅中吴鼎用各种媒介手段以及视觉、空间营造了一个冷静理性的场域。这似乎更适合去思考一系列与哲学、宗教、科学相关的问题。“圆”是一个完美的抽象概念,人类利用这个概念改善了自己的生活,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却不存在真正的圆,就像彩虹是模糊的,最精密的滚珠轴承也是不规则的。而相较于无法极尽抵达完美的圆,吴鼎的展览空间似乎以一种严密的把控方式让这个“圆”找到了最佳的闭合状态。它像是某个正在实施召唤的祭坛,将要建立一种沟通的渠道,将观众引向极致之地。

吴鼎,《关于圆的历史》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吴鼎,《关于圆的历史》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艺术碎片 对话 冯冰伊&唐潮&吴鼎&郑源
Q:
本次展览中,伴随着观展路线上铺设的绿色地毯,像是引领着观众进入一种电影般的叙事当中,而这个绿色却又是如此地醒目,不禁让人去思考题目“自然总是在逻辑中隐藏自己”,这里的“隐藏”似乎也不是消无声息的隐藏,我们应该怎样理解这里所说的“隐藏”?这是否也是一种对技术的隐藏呢?
冯冰伊:
我是出于对技术本身的考量来进行相关创作的,绿幕是影视后期中一种基本的抠像处理模式,在我们抠除这块图层得到想要的“有效”信息后,16:9标准化的方框内出现的是透明。虽然体现在最终结果上这块屏幕背景是黑色的,但其实不是,这可能就是我想带给观众隐藏却又核心的信息。
在制作的时候,我不会特别突出某个技术的使用,但我会特别遵从制作电影的态度或者状态去实施。比如电影中需要传统的抠像,或者需要运用的镜头语言,我会特意把它们做一些整理之后,再反其道而行之。我所认同的影像是戏法或者某种巫术,那么在我用最简单廉价的方式去揭示这种戏法背后的东西时,观众是不是可以得到由此产生的负负得正的思考?

冯冰伊,《SCP项目等级:爱与冲突》
多屏幕影像序列,混合媒介,时长不定,2019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比如我当时在时代广场上拍摄的行人的脸以及他们的状态,这其实和电影中的排演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展现出的效果却同样很戏剧化。我刻意保留了我面对陌生人时镜头的胆怯和无礼,但在传统电影工业中,这些似乎都是应该被藏起来的“拙”的部分。

冯冰伊,《SCP项目等级:爱与冲突》
多屏幕影像序列,混合媒介,时长不定,2019
包括《从洞穴中来》这件作品,大部分都是采用最简单的技术相关的方法来制作的,我会考虑前后图层的叠加,它不仅仅是时间性的魔术,更像是对于图像本身的解体。它们之间会产生效果,效果不得知,请大家给我回馈吧。

冯冰伊,《从洞穴中来》
双屏幕影像装置,彩色/有声,循环,2019
日常片段和传统技术的简单演绎和揭露,包括虚构出以vocanos的倒写为名字的滑稽哲学家,都是神圣的。

冯冰伊,《那个跳进火山口的哲学家》
影像装置,混合媒介,时长不定,2019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图片由作者拍摄

冯冰伊,《死与生先生》
影像装置,混合媒介,2019

冯冰伊,《混合演绎》
单通道影像,彩色/无声,5分钟,2019
Q:
“圆”本身好像就构建了某种迷宫。关于“圆”也无疑会让人产生一些宗教、哲学等等相关的想象,而这些可能又引向一种极致或者说终极的思考方式。就像是从思考的过程中一下快进到了终极答案一般,那么,当终极成为一种目的,过程是否就会被忽略?意味着无用?另外你为什么会这样在意“终极”?它是你认为的更为实际的问题?
吴鼎:
从“实在的维度”,到“极限的节奏”,到“关于圆的历史”,我的这些项目中有些东西是贯穿的,是有核心的,虽然今天我在做“关于圆的历史”这个项目,但后面也许还会有其他延续讨论的作品。我会去解决自身想要在工作上推进的一些问题,虽然观众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思考,但我通过我的展现,只是提供了一种可能性而已。

吴鼎,《关于圆的历史》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吴鼎,《关于圆的历史》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吴鼎,《关于圆的历史》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Q:
在你的展览空间中,从序:《雨点击目光》由视线进入,再最终回到尾声:《石榴和恒星》中再次讨论视线,视线发生的一方也就是观众似乎可以通过这个非真实存在的虚线构建展览的观看方式。但你也提到了视线虚空的本质。发出视线的一方并不会从被观看方获得某些回应。之前所构建的观看方式似乎又都不成立了。那么在这一进一出之间,所讨论的视线是否有不同?你认为视线是一种构建的入口吗?
唐潮:
视线确实是虚无的,但首先我将视线作为一种象征性放置在展厅中,其中很多的作品都是拍摄我自身的,这也可能是拍摄自己更为方便的客观原因而导致的,但也因为如此,我将这次的新作比喻成一个“人”的象征,它分成很多个部分,有10个章节,也就是展出的10件作品。从刚出生的时候对世界的第一眼观看,是比较纯粹的观看。因此作品《雨点击目光》中,只有一个镜头,因为雨滴的下落而不断地重新进行对焦,这是相机的眼睛,但在此我用来象征人的眼睛,而后的作品中,是将人类学习走路之前,爬行的过程转换成一个行为等等。整个展厅是有这样一个脉络存在的,而视线只是我们进入这些作品的一个入口,只是我们感官中的一种。最后其实更多偏向“视角”,是围绕“近”和“远”来展开的的故事,算是一种和解。另外,视线也与这次展厅的通道比较贴合,基本上可以一眼看穿整个通道。
 唐潮,“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唐潮,“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唐潮,《石榴与恒星》
双屏影像,4k,时长不一,2019
“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唐潮,《鳞片闪烁,像树略过火》
四屏同步影像,4k,3分19秒,2019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Q:
当时间再次被拉回到图像产生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图像会因为某种使用目的而被剪辑出来,剩下的就被剔除掉了,但这些被剔除的图像却可以在另一种方式中重现,也就不禁让人思考,究竟什么是正确的图像?以及被修改剪辑过的图像还是否具有精确性?
郑源:
在我的很多作品中我都试图去转移图像原本应该所在的位置,将他们重新挪用,组合,并产生新的意义。我并不想创造出一些前所未见的东西,至少在一些作品中,我更关注于如何在本来的可见中发现不可见的关系,并颠三倒四地处理他们。

郑源,《普罗大众之夜》
单通道⾼清视频,彩⾊,有声,29分17秒,2019

郑源,《普罗大众之夜》
单通道⾼清视频,彩⾊,有声,29分17秒,2019
在作品《普罗大众之夜》中,我同时在关注几个层面中的转变,一个是片中主角凯文曹身份的转变,从中国到美国,从一个暴力的呈现者到一个幸福的记录者,从镜头前的聚光灯下到一种在图像中几乎虚焦的状态,这样的转变对我来说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而伴随着这种转变的是他在两种身份下所生产出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图像,在片中我既使用了他当年做“脚斗士”时的电视转播,也使用了大量他到美国后所拍摄的婚礼影片。这些影片大部分是由他来拍摄,然后我来把他们剪辑成片,并收取325美元作为一个成片的报酬。所以在平行于他身份转变的同时,也是我在两种不同身份中对于图像的劳动:作为一个艺术家,但同时是个剪婚礼的,一方面我需要生产出一些,被称之为影像艺术的图像,一方面我需要生产出一些甜腻而幸福的糖水片,而后者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出现在展场中的,人们并不预期会在展场中遭遇幸福。如你所说他们可能并不是一些“正确”的图像,但让他们变得“正确”正是我试图在做的事情。

郑源,《一段简短的历史:中国西北航空公司》
单通道高清视频,彩色,有声,28分12秒,2018
“在半个迷宫中”展览现场

郑源,《图像研究》
单通道高清视频(1400×872),彩色,有声,7分49秒,2014
图片致谢艺术家以及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