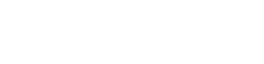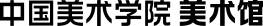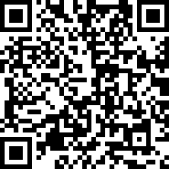时间上“当代”的艺术究竟在何种程度上堪称文化属性上“当代”的艺术?这是今日中国艺术家无法回避的课题。二十世纪以来中西两大艺术体系的相遇、碰撞,演绎出中国艺术在观念、语言上不断求新与试验的种种征候。通过对中国艺术现代之路的文化研究,可以梳理出一种与西方现代艺术性质上不同的“另一种现代性”,这方面大致已比较清楚。但是,伴随着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全球化”趋势的迅速蔓延,中国艺术还没有脱开“现代”的文化逻辑,就迎来了新的也即“当代”的文化境遇,艺术的基本问题由此发生了变化。对于这种变化,并不是每一个中国画家都及时敏感到并且主动地迎向挑战,甚至由于历史的惯性而拒斥实际到来的现实。
这种新的文化境遇可以称为“后主义”文化境遇。对属于文化性质的这个“后”字,以往我们的理解主要在西方艺术的“后现代”思潮上,这股思潮既是对西方现代主义的理论否定与样式修正,但又随着“全球化”趋势表现为全球性症候,引发出艺术的失序和混乱,特别是越来越趋于观念的艺术导致艺术本体的迷失,由此产生全球性的不亚于西方二十世纪初遭受现代主义冲击的“新的震撼”,对于有着自身文化传统的中国艺术,更是必然产生现实的文化焦虑乃至抵御性心理。但是,如果看到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形成的新的社会思想和文化上萌发的新的意识,我们应该看到,在一种普遍的“后现代”思潮涌现的同时,中国文化也进入了一种“后西方”的时代,那就是依托中国社会发展的契机,既吸收西方的经验,又对来自西方的影响作清醒的文化审视并采取策略性的响应。
“后现代”和“后西方”在中国的同时并存与相互激荡,便产生了一种处于动态的当代文化情势。在我看来,许江是能够把握这个动态的艺术家。许多年来,许江在中国当代艺术中扮演了一种“复合”的角色:时而是一位文化学人,对当代艺术的文化走向作分析研究;时而是一位艺术活动家,积极参与当代艺术的各种展览组织与策划;时而是一位言说者,在许多场合辨析艺术的焦点话题;时而是一位教育家,在艺术教育领域构想和推动适应社会文化需求的教学改革。当然,他的根本“身份”还是一位画家,他一向努力做的是在绘画中通达文化的当代境界。纵观他近二十年来绘画的历程,可以发现他是一位难得的通过文化思考形成绘画取向、又通过自己的绘画实验解决文化认识问题的思想型画家。“思”与“画”在他那里是一种生活的两种体现,都属于精神层面的活动。他的“思”,涉及到历史中的“西方”与“东方”的关系,其目的是“树立一种新的自我的文化史观,并以这种文化史观来勾联历史和当下的关系,建构自我本身”。他的“画”是“思”的形象载体,成为了当代文化情势的图像表征。严格地说,不能把他的“画”看成是关于某种题材或事物的描绘,而是要看到他的画作首先都是因“思”而必然和必要的形象流露,或者说,在他的画里,充满了思想的含量。
具体说来,许江在绘画上攒积起来的成果主要是关于城市和大地的风景。城市的景物是文化符号,大地的生命是自然符号,二者的义涵本分属两种类型,在许多画家那里情各有钟,但在许江的视野中却都同属于一个存在的世界。他喜欢研究城市,把城市当作文化的肌体,尤其喜欢追寻城市的历史,把一本本城市的传记读成历史的篇章,把城市的表像视为历史的片段,因此,城市在他的笔下成为画不完的对象,大者到与天际相接的城市轮廓与建筑躯影,小者到城市的巷陌、房屋的细节乃至道路的斑记。从绘画风格看,他的城市主题的作品都是史诗般雄浑和悲剧般凝重的混合体,他似乎无法为城市的现状勾画清晰的图景,反之,却像深陷在城市的梦境中感受正在消逝的存在。所以,他把自己笔下的城市风景称为“历史的风景”或“逝去与即将逝去的风景”。这种风景,与其说是“看”到的风景,不如说是“思”到的风景。而被“思”的也不仅仅是城市本身,而是作为文化集散地的历史。在他的笔下,柏林、上海、北京等等有着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城市是同一种性质的存在,他描绘着不同城市的景象,表达的却是同一种感怀。在这个意义上,他的绘画是从观察“形”本身升华到关注形而“上”的精神活动过程,他笔下的城市风景也是一种文化上的抽象性景观。
在视觉上与城市的风景对应的是大地的风景。在这个系列中,许江似乎换了一种心态,他做的不再是沉思的文章,而是行吟的诗章。或许从城市走向原野,他获得了远离历史重负的轻松,他因此可以随兴表达,去发现和捕捉许多生动的、转瞬即逝的大地表情。在那里有许多因生命蓬勃而引发的感兴和因四时变迁而触动的怜爱。相比起城市系列,他的大地系列画得视角多变、手法轻松、意趣活泼。由此可以说,他许多年在绘画世界里的心灵和情感就维系着城市与大地这两种生命情状,在“思”与“诗”、“话”与“画”的生活中交错穿行。
许江作品把风景这种传统的绘画题材画成具有文化主题的篇章,这就是许江精神上的文化超越。一方面,他取西方“后现代”思潮提供的“文化研究”视角,对既定的规范抱以怀疑,相信事物的不确定性后面有着可能生发的生命契机,绘画的目的不再是为事物作本质性的结论,而是使事物本质在追问的过程中浮现成形,在对客观世界的探寻中使自我这个主体得以验证。另一方面,他以“后西方”的文化策略克服了因追随西方艺术线性发展而产生的思想焦虑与文化隔膜,立足本土正在发生的、鲜活的现实,弘扬传统文化的丰涵大义,用一种“以中化西”的方式体现文化上的自信。他的艺术是“历史感”与“当代性”同构的艺术,其中的“历史感”,是与历史“活”在一起的彼此相望,其中的“当代性”,是凭借当代智识系统对当代文化问题作出的图像阐释。
对许江的绘画作如上文化意涵的分析,或许能够使我们看到中国当代绘画走出传统静态模式或西方样式的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作为画家的许江,在很多年里持续的另一种工作是克服当代图像世界带来的挑战。这是绘画在图像时代面临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问题是具有双重性的,一是如何在“图像的贬值”的境况中解决绘画图像的创造问题,二是如何在绘画图像中拯救图像应有的“精美性”。许江是当代“学院派”画家中最积极接触新媒体实验、倡导乃至研究新媒体艺术文化现象的一位。然而他艺术的立足点还是在绘画领域。他执意当一个“坚持架上绘画者”,去做“图像时代绘画何为”的文章。这是他在“新媒体图像技术迅疾发展,传统的绘画形态渐成危机”两极分立态势下的清醒选择,而他的绘画探索借助了这样一种两极对应的态势所造成的文化心理张力,找到两种不同的视觉经验的相关性,从而从绘画的自主性出发,缓解图像时代引发的绘画的“危机”。
“守望”绘画是今日许多画家的信念,但是,守望不是一种封闭的自我关照,而是守望者向外部“世界”敞亮自身并与“世界”共同“澄明”的过程,这需要集中解决绘画中“看”的方式。许江深知绘画上的“看”,不仅是视觉物理与生理的活动,也是一种社会意识的表征,所以他的“看”,是一种综合的“看”。从视觉的“看”的方式入手,他的绘画形成了“视象”、“心象”和“文象”三种品性的统一。作为西子湖畔“具象表现绘画”群体的倡导者和核心人物,他在以现象学哲学为方法论的视觉转换上投注了相当的力气,那就是在面对自然事物之时将陈规和经验“悬置”起来,使目光透过围裹在事物表面的杂芜,直逼事物的“本质”。在无碍的“视”刹然触及事物的“象”之时,事物的生命得以“澄明”。因此,他的画总是在抹去重来的过程中攸忽驻笔,在混沌中显现出富有内在结构的“视像”。为了克服单幅作品不能尽观尽兴的局限,他大量采用系列画面或连续画面,特别经常在小幅作品中采用十几、数十张小画拼接成一大幅画面的手法,用时间性的片断构成空间性的景观,以此获得对客观世界统摄的“心象”。他的作品在色彩上去繁取纯,笔法随性率意,用丰富斑驳的肌理营造出一片混茫的气息,使整个画面透溢出鲜明的精神性,呈现出了有文化学养的“文象”。
在许江最新的《葵园》系列中,一种整合的文化意识似乎更加清晰了。可以把这个系列看成是城市主题与大地主题的迭合,茂密的葵花如生长的城市建筑,更是大地上蓬勃不息的生命;也可以看成是画家行走与守望、思考与叙述的迭合。葵花的群像交织出生命的混响;系列的画幅不是一个系列的终结,而是一种向未来延伸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