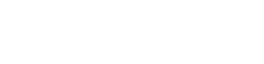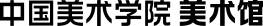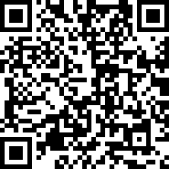斯文在兹
──将来语境中的艺文之道
孙善春
孔文子何以谓之文也?……
——《论语·学而》
心生而立言,言立而文明。
——刘勰:《文心雕龙·原道》
一
本展览关注艺术之为“文”:既遮掩,也言说。艺文之道,系于传统,活在生活世界;是历史的现实,生活的场所和道路。
斯文在“兹”:是这里,是当下,是时空中的历史语境,也是存乎其间超乎其外的理想与可能世界。而以现在谈论这个“文”,也是文的一种现实发生,一种文化的现场,一种艺术。“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与天地而参的人文早是一个世界,可以谈论,可以行动,可以生活。所以天地之心,成了“文心”与“人心”。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人言沸沸,言之凿凿,从古而今,“人文”变得越来越“文化”;照尼采这样的哲人来说,实在“太”文化了。有人说讲那么多,而大道至简。可是也论“道”日繁,正是现代人的生活实情,是人们的不得已。有谓“人心不古”,有谓“道心惟危”,有谓“文心失坠”,有谓“天心难测”,等等;但“天地之心”如何幽晦,文化之人们还得仰仗着那么多样的传统,或者在文言文,不管斯文坠绪茫茫矣。正如艺术家以艺为文,不停观察的眼,制作的手与体会的心。
二
文无古今,在畅其怀。
这首先说的,正是文“有”古今;入其心怀,才可能通达古今,畅其神思。
畅即通,通即乐。儒家孔子喜欢说“乐”:乐在其中,不改其乐,乐而忘忧,乐山乐水等。这样的乐,可谓永恒的幸福理想,于乱世中仍屹立不侵的。说到艺术之义时,所谓的“现代性之父”波德莱尔喜欢斯汤达的话:“美不过是允诺幸福而已。”作为艺术思想者的波德莱尔认为这种观点克服了“学院派”的弱点,正可以拿来探讨“现代生活的画家”;他的理想人物,不是“像农奴拴在土地上一样面对着画板”的画家,而是社会一切都入其眼将其吸引激动的“社会人”;他跳进现代都市生活的漩涡,充满热情,如一个年长的小孩,有好奇,有勇气,承受茫然四顾之后而来的种种人物与场景,只为寻得一点“现在”的美,因为他坚信这一点“现在”与传统中的所有“永恒”从来都不会分开。这样的现代画家寻找而再寻找,承担而再承担,但却醉心于现实生活,这正是现代艺术家的真实写照。这样一来,人心、文心与道心,才那么地被理想着,体会着,成为一条人生的道路;时至今日,成更成其为一种新的“传统”了。
于是,书与画,器与物,艺与道,皆在于一个有思想有怀抱的“我”:生活于兹,斯文与兹。原来道家所谓“道在屎溺”,也说的是屎溺在人生中的避不了。而儒家的圣人孔子说“泛爱众而亲邻”,也把人们轻轻地引入多人的生活日常之中。中国文化的根本是道教还是儒家?鲁迅曾经刺激国人面对这样的问题:大道幽微。而茫茫九派,流于生活世界,喧嚣纷扰,而又寂寂似无所说。
三
而文以载道。
文有传统体制。人们曾经希望,有些人怀瑾握瑜,把道说给人听,对某些人讲,清楚明白,直达人心。而艺之于文,也赞助化育,教化人伦。然而知识日盛,道心也就仿佛隐微了;这样的话,如今可说充塞了这个时代。而艺术与艺术家,却又成为了时代的前锋:他们是以艺近道,以感觉生活对抗着“太文化了”的现实世界。换言之,在艺术这里,埋藏着通向人之家园的真正的道路。
本次展览的艺术家,大都出身学院,或仍在学院体制之中。如果说现在人心是剖裂的,那么以为人在传统制度中的文化之人或者更为矛盾,更具“标本性”也许就有一定的道理:被寄予更高的期望来“承接”传统,却也脱不开这周遭世界,要以身“承担”着这时代性。以学院为“斯文”之重镇,可说是一种传统理想,只是现在也许更需要理清头绪:识者于此更能见传统之传与变,接绪与担当。比如诗书画三材会通,一律同品,如今安在哉;比如先前之文人画,以及“非”文人画。如黄宾虹就说:“中国有士夫画,为唐宋元明诸贤哲精神所系,非文人画可比。”而且作为“文化萌芽”的“图画”之发扬光大,则“端在士夫,责无旁贷”。时至今日,在当前语境之中谈文论艺,黄氏的“士夫”与“文人”之辨还是很难闪躲的大题目;哪怕只选择了他所分别出来的“文人”一路,也还是要面对千姿百态,还要斟酌损益,存乎自己一心的。原来传统之要义之中,还是这个“传承”的“承”字。没有这承受与承担,也就没有承接,无论是对永久之统绪,还是对偶然之现在人生。本雅明在他的历史哲学中对此不忘着笔,传统些的波德莱尔说是人的两面性,如当世之人,怀想着那日常之海那端的阿卡迪亚。这里,就是活“在兹”的人文了。于是,我们仍然期待“通三才之气象,备万物之情状”的艺术家,也期待这样的作品了。这里,有忘我的欢乐,也有的是深刻的孤独。
四
各道其道。
在这里的十数位“学院”艺术家里,可以看到许多的探索:分裂与痛苦,追寻与渴望。在他们这里,可以感受到翔舞于其间的艺与文的精神:每个人都是一个载体,一个舞台;而许多人一起,就成了一个场域,一种生活。传统与现在,艺文与人生,每个人,都如哲人所言“同时在两条河流游泳”,这话也或许可谓孔子所说的“游于艺”的广义注解。比如,鲁大东博士的伪碑书法作品,不仅是对正典书法文化传统的调侃,也是一个对现代消费社会文化现实的响应与呈现;书家本人的“跨界”音乐实践,也只是“文人传统”的一种现代演练,若上溯到古时书家的得意忘形、解衣磐礴等,实在没有多少异数可言。曹晓阳教授的木炭山水曾经于国内展出,引来相当的注意,无论是西画家还是传统的山水画家。因为他有意突破所谓的“水墨”,而径取“精神”而为之,以一己这个现代艺术工作者所受的所有教育为工具,直面自己精神深处的山水图像,这种自我探寻甚至可视为“自我折磨”,但他这种与传统的执拗的“肉搏”却颇令人动容。
井士剑教授系油画名家,但也舍笔动手,装置雕塑无所不为,或如古人所谓但求适意耳;同样出身油画的楼森华则是左手国画右手油画,他对黄宾虹有着相当的研究,观者如果细看他的国画与油画两个版本的作品“白龙潭”,当能对一位诚实于绘画精神与传统的当代艺术家的追求有所感怀。而周刚“灼灼其华”的矿工,则能逼视观者的眼睛:这正是波德莱尔氏常言的现代生活,里面蕴藏着某些绵延而今的东西:一种对生活各种“锋芒”的正面相迎,这里热情的生命感仍旧激荡着这个世界。
各道其道。西人谓“条条大道通罗马”,其致一也:艺文之道,传统之所系,都在于每个艺术家都是活生生的个体,却也各自为战,各行其“是”。如何“体道艺之合,究圣哲之蕴”,终于“大道万端而归于一”,在艺术家那里,成为赤裸裸活泼泼的生活。在这里,“艺”之为“术”,“艺”之为“道”,终合于面对生活世界的身心“制作”:我们面对刘正教授的雕塑作品,心中涌动的情绪感怀,不也正是同于韩天雍教授现代书法的语汇?这暗涌在十数位艺术家作品之中的,激动我们的,正是来自深沉处的共通的传统,美感或精神。
五
“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
我们的文,历来常是遮风挡雨,与世无争的故里之家,是躲进其间就可以成“一统”的小天堂,比如传统,比如文人,比如学院,比如永恒的美等。但是家,也是时光之海中的一点光,一叶舟。它承担人更多的感情,也要求人更多的承担。是的,承担。就像那位诗人所说,当从宇宙高空俯视这小小的地球之后,你如何再来寻求茅屋的庇护。艺文之道,也正如奥底修斯的茫茫生命之海上的漫漫返家之旅,这旅人心中,伊萨卡岛鲜花繁盛。所以,还家,是一条道路;而家,是弥漫于生活之海上永久的乡愁。
“客里似家家似寄。”
于是作为文化的艺术,诉说着传统的永恒,与每一个生活当下的偶然过往。写下此刻,已成过往;寄意过往,遂至将来。主题中出现的“将来语境”自然与此有关:关乎每个艺术家,关乎许多人为之心系的传统之流,也关乎许多人交织勾连的生活世界。这不仅是因为传统之流来自往昔,经由现在,流向未来;还因为艺术家不仅描画斯在当前,“忧生伤世,持志缘情”;也就“合乎自然,邻于理想”,也都期望着将来,预示着未来。传统在我,斯文在兹。正如黄宾虹先生当年所说:“挽回积习,责无旁贷,是在努力者有力为之耳。”于是,“内修心而外益世”,“抒胸臆以振斯文”,就有所望于艺术家与为之激发感动的观者群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