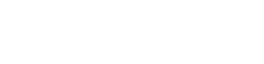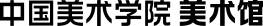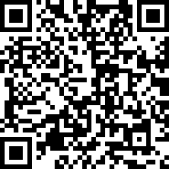上海博物馆藏南宋李嵩《西湖图》,“宋韵今辉”艺术特展展品
对于中国的古人来说,所谓诗情和文艺的根本是人与世界的兴会,这种观念所孕育出的艺术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山水”。这些年来,我多次讨论山水问题。山水,不止是山水画,也不止是诗情画意的山水,而是作为经验的山水,作为世界观的山水,我希望在山水中重新唤起我们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感-观和感-觉。
中国画自其发生伊始,就牵系着中国人独特的世界观和思想系统。作为一种“世界观的艺术”,中国山水画最本质的是它的观物之道。观,是人与世界包括人与自身之间最根本的一种状态,超出了视觉观看的意义。
宋人感物兴怀,神与物游,穷情写物,所以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一切都能成就画意;气之动物,物之感人,一切皆可摇荡性情。两宋绘画,远超乎宗炳所谓“以形写形,以色貌色”,更进一步“以心为境,以神写形”。因为究天人之际,人心通于天心——人心之通于天心,即是无处不有大观照,一花一叶,俱有安放,才是本来。宋人相信天地间无处不是自在完全,才能如苏东坡所言“不留于一物,故其神与万物交”。
印宗秦汉,书宗晋唐,画宗两宋。从五代到北宋的山水画家与后世的文人画家全然不同,他们经过对山水林泉的切身关照和长期体察,表现出浑然天成、自成一气的高山与壑丽。
范宽的《溪山行旅图》堪称山水画历史上最伟大的纪念碑。这件作品最关键的是它的静穆,它的沉默。画家的笔法尤如一场大雨,迅疾淋漓又沉着痛快。这山峰如此凝固坚实,又如此富有张力。主峰挺立,沉默无言,旷古如是。那山中行人其实看不到巨大的主峰。虽然主峰占据了画面的主体空间,虽然它已经在那里矗立了亿万年。与《溪山行旅图》相较,李唐的《万壑松风图》虽然更为硬朗深秀,却没有这份沉默的力量,太古的寂寥。
所有的研究者都为北宋郭熙《早春图》复杂的空间构造赞叹不已。画面中的丘壑营造、阴阳向背、起伏开合,都极为精妙,这真的是宇宙构造的技术。郭熙的山水画论《林泉高致》,是中国古代画史的里程碑。从这部画论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宋代山水画家对自然世界是如何的体知入微。
两宋绘画,丘壑谨严,万象森然,其状物之精当,意境之高妙,令后世叹服。面对宋画,我常常想:在没有照相机的时代,宋人如何从眼目之所见,表现出如此丰富微妙的物像,创造出如此具有“世界感”的意境?我以为,唯有对自然理法的深刻把握,才会如此体知入微,唯有从自然理法中演化出绘画理法,才会如此刻画入微。这背后,有一种观照世界的独特路径。宋代哲学家邵雍说“以物观物,性也;以我观物,情也”。宋代理学倡导“格物致知”,不独以我格物,而且以物格我。天人之际、主客之间的丰富意蕴和微妙关系,尽在宋画的情致意境之中。
纵观历史,画宗两宋。北宋之理、南宋之情,创造出令人流连颠倒的无尽气象,也成就了人与世界的一场场兴会。两宋的画家们既能够为宇宙造型,又可以为万物写照:山水画的层峦叠嶂中蕴藉着宇宙太古的广大与寂静,花鸟画的写真妙趣中更有着自然造物的千般生意、万种风情。宋人缀风月,弄花草,务求工致妍美而又清新灵动。他们用戏藻游鱼刻画水波的柔媚荡漾,以柳荫牧牛抒发一片江南的田园生趣。他们描绘春日水滨、华服冶游,穷妍极态,彩丽竞繁;他们刻画古木寒林、苍苔幽径,寒气满纸,天地寂寞。宋画中有天光云影,龙蛇起陆,神变无穷,幽微难测,既有《溪山行旅图》的雄浑,又有《万壑松风图》的森然,既有《早春图》这样“致广大”的宇宙气象,又有《雪竹图》一般“尽精微”的特写镜头——《早春图》以全景山水展现出造化之理,《雪竹图》却让我们体会到一滴水中亦可映照出整个世界。
如果说北宋绘画,是在层峦叠嶂中展开空间的一种全景式的综览,我更愿意称南宋山水画,是一种“特写”的山水。
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宋韵今辉”艺术特展中,我反复揣摩这些名家真迹,最大的收获是对两宋的画风之变有了一些新的体认。南宋四家中的一个关键人物是李唐,李唐是“四家”里年纪最大的,在北宋时已经名满天下。迁都之后,面对江南山水,渐渐展现出明显的构图变化,从其《濠梁秋水图》便可以得窥一二。南方山水跟太行山等北地山川全然不同,北方雄强壮阔的崇山峻岭所形成的图式和画法,不太适用于画南方山水。南方多是草木华滋的丘陵地貌,水系众多,到处是“一江两岸”、层岩幽壑,画家们在游历山川的过程中获得了一种新的观照状态,呈现出一种与北宋不同的“特写山水”。
北宋画家大多是在游观综览中按照“三远法”构成全景山水。《早春图》最为典型,所谓“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画家在群山之中周游遍览,每走到一个地方,那里的空间就会被充分展开。宋人讲究“丘壑内营”,无数展开的局部空间综合在一个画面上,画“境”远远大于我们的正常视觉,可谓四通八达、千变万化。这是一种空间的拓扑学,台湾学者陈传兴称之为“代数空间”,面面中仿佛蕴藏着若干个洞天,明豁奇绝,境界广大,真是纳须弥于芥子。
南宋山水画有所不同,南宋开始出现了“景”的观念,其本质是从连绵世界中剪裁出诗性空间,一个个以诗性命名的山水景观。夏圭的《溪山清远图》就是典型,一幅手卷绵延不断,诗意的景致纷至沓来,真是溪山无尽,山高水长。
南宋山水画本质上是诗意画,画家们身寄山川,感受着山水的动静变幻,画家的身位也发生了变化,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观察者的视线从永不停歇的巡游中逐渐安定了下来,静观默会大自然的诗意。不再是“山形步步移,山形面面看”,画面上出现了确切的视点。画史常说马远、夏圭的作品是“一角”“半边”,暗喻南宋偏安一隅,山河不得整全,这多是附会之辞。我认为其实是江南氤氲迷离的山川风貌唤起了画家们内在的形式冲动,在静观山川景物的过程中引发了一种新的体认。于是,一种全新的构成意识被唤醒,一种极具形式感的绘画图示被创造出来,这就出现了一种“近景山水”,一种山水世界中的“特写”。我认为历史上,真正伟大的作品,每一件作品都是对世界的一次发现,而这些画家就像这个世界的发现者,同时又像绘画的立法者,这才是真正的伟大。
我们讲“特写的山水”,刘松年的《四景山水图》就是佳例。南宋有“西湖十景”,就是西湖的十个特写、十种诗意情境。美学是感性之学,南宋的感知之道和感性之学有着一种特写的状态,西湖十景的空间构建也是这样。《四景山水图》中,我个人偏好是冬景那幅,天地静谧,雪意萧萧,但并不荒寒。尤其是三棵青松,在一片雪景中透露着深秀沉郁,雍容大气,无比精神。远山的轮廓线美极了,充满了音乐性。台阁屋宇、断桥行旅,一切都被安置在真实妥帖的一方天地之中。
宋代绘画特别有一种“世界感”。看《柳下双牛图》,我们会惊叹于画家对柳树的精妙刻画,对芳草平芜的妥帖表达,更令我们感动的,是在这个小小的团扇中一个世界被如此完整地建构起来,画面中的那一缕初春的微风似乎吹拂着所有事物。画家以意写境,画中世界悠远静谧,虽然是天地一角,却自在完全。这八百年前的一瞬,依然隽永清新,仿佛一切都正在发生。
画宗两宋,宋画“以一当百”,讲的既是它的珍贵价值,更是因为它的丰富、它的精微。后世画者无不为之辗转反侧,无不对其心摹手追。此间种种,需要我们从本次特展中面对宋画真迹细细体味。
(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浙江美术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