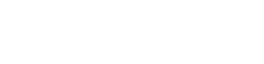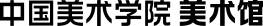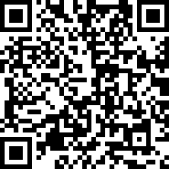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后赤壁赋图》(局部)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为辉煌的年代。
我们之所以说宋韵辉煌,是因为有宋一代,卓立着一大批震烁千古的文化大师。这些大师中有司马光、欧阳修、三苏父子这样的千古大家;有周张、二程、朱陆这样的宋儒理学大师;有范仲淹、王安石这样锐意新政的干臣;有花间派、婉约派、豪放派、格律派和北宋三家、南宋四大家的万斛泉涌的诗词高峰,正是这些民族的精英,汇成了蔚为大观的千古风流,汇成被誉之为中国两千年中古社会的文化巅峰。
我们之所以说宋韵辉煌,更因为宋代历史上文化昌明,诗、书、画熔为一炉,出现李成、范宽、郭熙、赵佶和后来的刘李马夏为代表的院派画家,开创了苏轼、文同、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士人绘画,构成了画与诗相提并论、人品至上、心与物游、言外有意的儒家美学体系,铸造了影响千年的诗、书、画一体的文人世界和品鉴标准。他们丰沛的创造至今都能够供我们卧游与畅神,都是艺者学习和修养的榜样。
一
十多年前,我曾经做过一个观念性的拇指微电影:一个背立的身影在观看北宋范宽的《溪山行旅图》,镜头迫近,越过背影,逼入远山的局部,墨点隐约可辨,肌理依稀交织。接着,镜头渐退,“溪山”变作真山,最后回到背影先前的位置,但其所对的已成美院山门之外的青山。这个拇指电影以游戏的方式述说一个道理:我们要理解中国传统的山水眼光,进而用这种眼光观看我们周围的真山真水。什么是山水的眼光呢? 中国人看一座山,在山脚下住一段时间,在山腰又住一段时间,山前山后来回地跑,又无数次登上山岭远望。最后整座山了然于心,待要画时,和盘托出。一画之中,山脚与山体俱见,山前和山后齐观,巅顶与群峦并立,所谓高远、深远、平远。不为透视所拘,不受视域所限,山水草木一例相看,烟云山壑腾挪反转。这种方法,古人叫饱游而沃看,游目而骋怀。山水眼光是一种不唯一时一侧的观看,更是将观看化入胸壑,化成天地综观的感性方式。这个戋戋小品意在呼吁将中国传统活化在日常观看中,将山水之观化作我们观察世界、理解自然的感性方式。
青衿之志,履践致远。远在孔子的治学的学苑里,他曾问理想于众弟子,各位弟子都谦恭地谈说了自己的理想,孔子并未首肯。最后问到正在鼓瑟的曾皙,曾皙果断地停下手上的弹奏,铿止,答日:“暮春时节,春服既成,吾与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正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时节,着新成的春服,在沂水中沐浴,迎着风舞蹈,高歌而还。孔子听后不禁喊道:吾与点也。孔子欣然赞赏的正是曾皙的无名之志。而这种志向正是中国人与自然长相浸润、与时同乐的生命艺术。
山止川行,风禾尽起。中国人的心灵始终带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山水的依恋。何谓“山”? 山者,宣也。宣气散,万物生。山代表着大地之气的宣散,代表着宇宙生机的根源,故而山主生,呈现为一种升势。于是,我们在郭熙的《早春图》、范宽的《溪山行旅图》中看到山峦之浩然大者,在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中看群山延绵,陶然不绝。
何谓“水”? 水者,准也。所谓“水准”“水平”之意。“盛德在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相对山,水主德,呈现为平势,和势。于是我们又在《千里江山图》《富春山居图》中看到江水汤汤,千廽百转。荆浩有言:山水之象,气势相生。山水绘画,正是这种山水之势,在开散与聚合之中,在提按与起落之中,起承转合,趋背相异,从而演练与展现出的万物的不同情态、不同气韵。
山水非一物,山水是万物,它本质上是一个世界观,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综合性的“谛视”。所谓“谛视”,就是超越一个人的瞬间感受的意念,依照生命经验之总体而构成的完整的世界图景。这种图景即是山水的人文世界,它是山水的“谛视”者将其一生的历练与胸怀置入山水云霭的聚散之中,将现实的起落、冷暖、抑扬、明暗纳入内心的世界观照之中,形成的“心与物游”的整全的存在。
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展览的“宋韵今辉”特展中,展出了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之《剩山图》卷,《富川山居图》卷的主体则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黄公望先生身高几许,却能将一条江的蜿蜒回转、山水情势画成山居一卷,能以一种天神的高度,俯览万里,掇拾山河,他所使用的恰是这种游目玄览的方法,所驰骋的正是这般山川映带的胸壑“谛视”。
二
多年前,我曾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亲眼见到了郭熙的《早春图》,它是画在薄绢之上,它或者曾经拥有淡雅的颜色,一千年的历史岁月,把它煮成了今天的沧润的褐色。它是用中国的毛笔蘸着烟墨和自然材料的色彩绘成的。我们仿佛在这里看到一片奇幻的山壑,被一层层的烟云包裹着,宁静而悠远,峻拔而生机勃勃。这是早春即将来临之时的山中景象:冬去春来,大地苏醒,山间浮动着淡淡的雾气,传出春天的消息。所以这张画被叫做《早春图》。
如果我们再进一步细看,远山重峦叠嶂,气势雄拔;近岗怪石耸立,古木参差。那些古木,招展开它的枝杆,显出它的傲然兀立的身姿。这可能是世界上最有神气的一片树林了。树木正在生长着新叶,一片春天的生机。在中央高耸的巨石两边,都有奇妙的山水,左边巨石的下方是迷濛的水面,一家人正从船上蹒跚而下,顾盼有致。在盘桓的山腰处,有农人披着蓑衣,负担行走。而在右边,一个瀑布叠着一个瀑布,注入桃花潭水,流瀑之上是一片飞檐陡壁的建筑。这分明是一个隐身在群山中的屋宇。让我们再举目向上望,山壑翻转而上,烟云渺绕之间,层层峰峦隐隐出现,那峰上的树木迎风招展……。
我们感到沿着这画,行游在山下山上、山前山后的风景之中,我们感到这山和树、水与烟都是春天里的活的景色,我们可以在这些景色中观赏、游玩、居住,与天地相往来。这就是中国绘画,这就是中国山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一个风景,更是遭遇一片风景的世界。我们被打开的不是一个镜头,而是持续不断的、使我们的身体在这里穿梭往还、使我们的心在这里吐纳元气的观看与体验。这就是与西方绘画、与今天照相技术全然不同的中国绘画。
在这些生动苍润的描划之中,我们还感受到了笔和墨的美,这种美最能体现山水的形神,我们还能从这些活脱脱的笔墨中,感受到一种游戏的意味,见证一种人性的风貌。正是这种“戏墨”的方法,最自由也最有效地把我们带入那个“象”的体察之中。这个“象”既不是自然对象,亦非纯然意识里的心象,而是自然对象与纯然意识之间的辽阔无际的间性的世界。我们在这种“象”的体察中,走进了中国绘画的世界,走进了人的诗意地栖居的世界。中
国绘画让我们获得体象的诗意,生命的诗意。我们正是沿着这张《早春图》的可见的观看,一步步地走入感知的深处,走入中国山水精神的不可见的深处。
三
二十世纪的文人在论及宋代艺术时,往往乐于将画与诗相提并论。他们一方面力图用文学的品鉴形式评说绘画,另一方面绘画也被作为文学的图解方式,让我们一起来展阅北宋画家乔仲常步苏子诗意所作的长卷《后赤壁赋图》,画卷冷月浮影,朦胧拥塞,山水登高,涉水行远,以连环描叙的方式将赋的描写联成一幅长卷。既有“行歌相答”的快意,又有“划然长啸”的肃然,野逸而鸣高,揭示了苏轼的激情与悲愤。乔仲常用画卷,与苏轼,与千年后的我们,素墨写景,纵笔唱和,共赴千古邀约。
在尺幅之中,我们共同登临胜迹之境。孟浩然诗云: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乔仲常把苏子的赤壁画了下来,我们在画卷中登临。全画用山峦树石,分成几阙,苏子数度显身。山高难画,以林深代之。这里林木充塞,悬崖上像一个洞,有栖鹘之危巢,有深不可测的幽宫。这是乔仲常的妙笔。又然后是在山上,划然长啸,山鸣谷应,却不期然地悄然而悲,肃然而恐,凛凛然觉得不可久留了。接着回到船上,放任中流。时已夜半,回顾寂寥。画面由拥塞变得简阔。此时,有孤鹤横江东来,双翅如轮,戛然长鸣,掠予舟而西也!整张画翻转有序,陶然大气。我们随着苏子的身影,登高涉远,在山水中穿梭,在吟叹中相会。乔仲常的画卷令山川皆景,草木俱神,让生命的悲欢、流逝的嗟叹、山壑的深邃、云气的苍凉,俱在此时此地相聚,断石、深崖、虬木、孤院凝在一起,供吾辈远眺瞻望,并始终合为一体,蔽藏在山水幽茫的深处。在此长卷的巡览中,我们又仿佛进入怀远之境。“今古一相接,长歌怀旧游。”我们已经读过苏子的前后赤壁赋,通过文本的阅读,有过自己的想象。现在,在乔仲常的笔迹中,我们依稀重访故地,由于心往神驰,而与古人在精神上契合,并由此完成与远方故人的怀念与兴答。
这长卷还是御风陶醉之境。前后赤壁赋,从始至终,皆有酒。古今皆然,酒酣耳热之时,容易放
任纵浪,直入陶然醉酡之境。乔仲常似无醉笔,却也提按风雨,使转烟云,全画分为四段,第一段是行歌相答的洒然,画面抒阔,笔墨简远。第二段江流有声、划然长啸,那是一种肃然,画面拥塞,笔墨锵然有力。第三段放任中流,那是一种飘然,画面格外简远而开阔。第四段是梦遇与惊寤,那是一种朦然,画面渺远。四段表情各有不同,但墨色素笔,天然地带有一种月夜情愫和朦胧想象。笔墨简淡素朴,尤见其变化。中间肃然的一段,那皴法如龙如虬,点划如钉如豆,一林映带百千林木,一石翻卷百千山壑,掇集而成一种神秘风气。山水的吟诵和生命的洒然同时从四方涌来,又始终蔽藏在横卷叙事的深处。此所谓陶然御风。直若当年柳宗元登西山的陶然醉语,“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读乔仲常的长卷,我们如登如上四境。此四境,交揉叠错,彼此诱发。看似一己的感怀,却是千古的集体经验与情怀。起兴在展阅之间,唱答越今古千年。我们如踏先人与众人的踪迹,逐迹而行,将自己一次次地泊锚于这一片因文本阅读而“经历”过的历史现场,长相浸润,情似赠,兴如答。
四
在宋代,又有一类文人画家,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大诗人苏轼。苏轼可以说是学者型艺术家的最高典范,是学术识见与艺术造诣结合最好的一位。苏轼置身从中唐韩愈开端至北宋的文化运动之中,以“才气”、“豪气”之担当聚文、道于一体的文化模式,提倡新学术、新创造。苏轼第一个提出“文人画”术语,以应对画院的专业画家。他写道:“观士人画,如阅天下马,取其意气所到。”他在绘画的题写中多次题到:“文以达吾心,画以适吾意而已。”作为诗人,苏轼对绘画强调天机,强调诗心独创,但他并不贬低“艺”的重要性,极重视有道有艺,道艺结合。他写道:“有道而不艺,则物虽形于心,不形于手”。苏轼在《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中畅言:“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识其所以然。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过也。”如何解决这个
问题? 在论艺的谈说中,他反复引用《庄子》中庖丁所言:“臣之所好者道也,近乎技矣。”他的意思是:他所关心的是“道”,这个“道”已进入他的技艺之中。他已经到达适当的状态,并把技巧抛在脑后。这种状态意味着已将技巧的运用提升到道的高度。苏轼诗言: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 他的“凝神”描绘了一种入定状态,以《庄子·达生》的梓庆削木为鐻的故事,来言说“以天合天”的道理,提倡文人绘画入神、传神的境界。
苏轼的绘画,传世稀少,于今所见,只有《枯木怪石图》与《潇湘竹石图》。那枝干虬屈无端倪,石皴亦奇怪。为什么是枯木怪石? 为什么木要枯,石要怪? 因为枯木怪石无定形,利于放笔,笔墨生骨,便于造形,以发胸中盘郁,以求英风劲气逼人。据苏辙回忆,苏轼早年在凤翔,常入开元寺观壁画。“往之匹马入寺,循壁终日。”开元寺壁画有吴道子的双钩薄彩,也有王维的墨竹,用墨笔直接撇出形体,令苏轼特别心仪。文同的“墨竹”,对苏轼的影响最大。那一曳垂竹,从上而降,却布青云之势,赋予苏轼最深滋养。在《潇湘竹石图》中,三株青竹,两块顽石,一抹潇湘林影。烟空中,青竹飘撇无定,任意东西,正是风烟俱静,天山一色的意境。点划放意,石皴挥洒,淋漓斑驳之处,摇曳着岁月流殇。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最具超逸的韵趣。
宋代著名画家黄庭坚诗言:“一丘一壑可曳尾”。“曳尾”指《庄子·秋水》中的那只乌龟在泥沼中自乐。一丘一壑,则是寄情山水。人在山水中,自足自乐,表现出传统文人尤其是隐居文人的纯粹与高尚。一丘一壑作为成语,可以追溯更为久远。《汉书·序传上》有言:渔钓于一壑,则万物不奸其志;栖迟于一丘,则天下不易其乐。此言之意在于垂钓一壑,栖居一丘,坚守良久,不改其志其乐。一丘一壑虽有限,却以某种坚固的深度,唤起恒远的积极思想,赋予人以自足自乐的充溋,“风乎舞雩,咏而归”的无名之志。这直接构成了山水世界的无边容量与意涵。
心存气象,素履以往。我们讲宋韵,宋韵的根蒂在哪里? 南宋诗评家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言有尽,意无穷,或者说用有限的言,抒发无穷之意,这是宋代诗画要达到的境界。在中国理学的观念中,真理只能为有悟性的心灵所辨识。朱熹有言:尽其心可以知性知天。当卓越的心灵映印出自然影像,这比未经心灵解释的自然更加真实。这样的艺术就揭示出了视觉世界的可信形象。这正是宋代诗人与评论家所悉心追求的蕴涵,也是我们筹划和组织这个展览所时时铭记的。
所以,我们要举宋韵文化的旗帜,深耕江南的人文沃土,重织宋代文人的夯劲秀美、情兼雅怨的文化品位,在宋韵文化的源头去重新接续民族的博大精深的文化气息,与古携新,从流激荡!
(作者为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中国美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