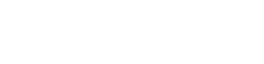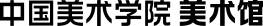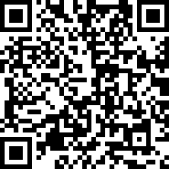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夜山钩古”黄宾虹作品展厅一角

《夜山图意》
800年前,南宋宫廷画师李嵩在《西湖图》里,用淡墨染出整片北山。当时还没有北山路,湖岸山居连成一片。而在西泠桥的南边,他分明画出了一条小路。这条今天西湖边的小路,叫栖霞岭。
岭上31号,20世纪绘画大师黄宾虹先生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最后7年。也是在这里,他完成了伟大的“衰年变革”。
800年后,正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进行的“宋韵今辉”艺术特展中,李嵩《西湖图》在一楼“宋韵”主题展“湖山揽胜”中展出;楼上,黄宾虹和潘天寿两位20世纪大师的山水作品,作为“今辉”呼应展出。
往后退两米
相比一楼的许多宋代名作,二楼“今辉”部分黄宾虹先生的画,显得不易读懂。这个困惑,早在80年前,宾翁第一次办个人书画展时,就有了。
1943年,翻译家傅雷为曾经同事过的宾翁策展了“黄宾虹八秩诞辰书画展览会”。画展期间,傅雷几乎天天来到会场。他很注意观众们的反应,有时还与他们一起读画,一起探讨研究。观众每有疑问,傅雷便热忱地解答。
后来,傅雷还化名“移山”,写了《观画答客问》一文,以传统文赋的主客问答形式,虚构一人观看黄宾虹画作后疑惑不解而发问。
傅雷先生首先替非专业的观画人问出了心里的一大疑惑——客:“黄公之画,山水为宗,顾山不似山,树不似树,纵横散乱,无物可寻,何哉?”站在黄宾虹先生的画前,啥也没能找到,山看着不像山,树也不像树,只看到散乱的笔笔画画,为什么?
傅先生赶快带着你往后退几大步,你站得太近了。咫尺距离,不是看画的方法。为什么不试试远眺?
逼视着宾翁画中的大山水,只能看到局部的山石纹理,树干枝桠,怎么能感受得到烟云出没,疏林密树的峰峦气势?这就是我们最熟悉的道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前几天,浙江省美术协会副秘书长李云雷带朋友在马远的《松寿图》前观看时,建议大家往后退两米,“遂见骨骼清朗,愈远境愈深”。“同样看宾翁老人画,近看一片混沌,远观丘壑万千。”这是黄宾虹对宋画的一种回应。
“往后退”也是今人对西方绘画的习惯看法。而当年傅雷给黄宾虹的信中,就已经多次用西方现代绘画来类比黄宾虹的作品,以论证中西绘画精神并无二致。
在“宋韵今辉”展厅,大家还可以继续往上走,到三楼“含英咀华——绘通中西的国美油画”展上,领会傅雷先生说的这种中西绘画殊途同归之妙。
从白宾虹到黑宾虹
黄宾虹先生的山水,尤其是晚年的山水,是一片黑色的。说得再准确一点,是墨墨黑的。
业界把先生后半期艺术人生归纳为“黑宾虹”,与早年的“白宾虹”相对。“黑”和“白”,这次展览都能看到。
由“白”转“黑”,大约是在先生花甲以后。1933年春天,70岁的黄宾虹应四川美专讲学之邀,来到成都,不料学校因战乱停课,他决定到西南面的青城山看看。
有一天晚上,黄宾虹无意间注意到白天秀丽的大山,在夜晚显得格外神奇:在月光下,有些地方只剩下黑色的轮廓,有些地方却呈现出银白色。逆光下的山林,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光环,放眼望去,凹凸分明,变化微妙。
黄宾虹马上意识到,北宋人即多画阴面山,如夜行岩壑间。由此他的内心获得了极大的开启。后来,他经常入夜携笔游走山间,在月光中画素描。
1937年,宾翁前往北平任教,不料刚到北平就爆发了卢沟桥事变,由此开始了他在沦陷区伏居的11年生活。这11年间,除每周二的讲课外,黄宾虹闭门谢客,专心研古,完成了由“白”到“黑”的转变,画风开始变得黑密厚重。
在今天的“夜山钩古”展厅,美术史研究者陈可对着宾翁1954年创作的《夜山图意》,越走越近。“从前看画册,或者博物馆里看真迹,隔着很远的橱窗,总有一种不真切的感觉。今天这么近距离仔细看的感觉太震撼了。我已经不断地在向宾翁道歉了。”
陈可读过黄宾虹对宋画的学习笔记,却从没有感到宾翁的画面与宋画有真正的关联。这次,因为近,他才看清楚画中每一笔每一划,尽显宋人的精微。这树、山、坡、屋、水岸,分明在楼下“宋韵”展厅见过。
黄宾虹的夜山写生,在月光照射的地方都留有空白,一笔不画。有的非常细微的留白,宾翁直接用笔圈起来——这块白是不允许弄黑的,不要说脏墨,淡墨也不能进去,直接留白。暗处则沿山谷岩壁的轮廓进行勾勒,然后在里面层层加黑。
这一层层累积的浓黑墨色啊,浓到黑到什么样的程度?中国文联副主席、浙江省文联主席许江说,像打翻的墨一样。“但是他并没有完全都是黑的,他一定留下了飞白。这种飞白把墨色的华滋给衬出来了。”
看不见了,如何能画
栖霞岭31号的院落,黄宾虹人生中最后一个居所。自从1948年离开北平来到杭州后,他就住进了这里。
浸淫在江南的风物之中,宾翁逐渐深化了在北平时期就已形成的水、墨、色的探索,画面完全呈现出江南自然山川草木的华滋,充满了水汽氤氲之趣。
然而沉迷于这种田园诗般创作生活中的黄宾虹,在1952年4月被确诊为白内障。这种疾病非常痛苦,不但要忍受双眼针刺般的疼痛,视力还会受到影响,直至最后完全失明。
得知宾翁生病后,时任艺专校长的潘天寿先生专程前来探望,到了家里发现,宾翁仍然借助放大镜在摸索着作画。随着眼疾不断加剧,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近失明,宾翁仍然每日作画。
他的笔触是否到位,构图是否符合章法?可能已经全然不知。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完全无法创作的状态下,黄宾虹先生又把自己的绘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看不见了,如何能画?他必须用最浓最黑的墨,而且在一笔一笔之间留出了白。他靠黑和白的强烈对比,他的眼睛才能依稀地看到变化。这时候他是用心在画。
今天,也只有走近先生画中的西泠、西溪,你才能发现:他的墨黑,也许有100个等级——往纵深里不断累积的层层叠叠,任意纵横,又笔笔分明,笔笔生发。
过50年才有人看得懂
对黄宾虹来说,画画似乎永远是一种探索。如果有了新的感悟,他就会把多年前的作品拿出来继续完善。
然而,在他生前大部分的岁月中,时人将黄宾虹视为美术史家、社会活动家、鉴定家,却鲜有人认可他的绘画。
据说先生弥留之际,他曾对身边的亲人说:“我的作品要过50年才有人能看得懂。你们看着吧。”
2023年,按照宾翁自己的算法(周岁加两岁),他今年160岁了。我们有没有更加懂得一点老先生的天真,他一笔一划里高度的自由和开放?
“宋韵今辉”特展还有一周。请大家去看老先生们的作品,退远看,走近看。你会遇见大师,遇见不同时代、各种面貌的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