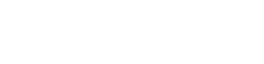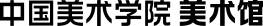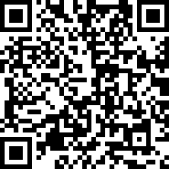这是有风君第二次,去看赵无极先生的这场作品展了。
记得第一次去时,杭州亚运会还没开幕,在人山人海的现场里,有风君只知道赵无极是著名的华裔法籍画家,是西方现代抒情抽象派的代表,是最具世界影响力的华人艺术家。
而这场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的“大道无极——赵无极百年回顾特展”,是亚洲最大规模的赵无极回顾展,其中展出赵无极的油画作品129件,加上其他重要作品和相关文献共200余件。


展览海报,中国美术学院提供
作为一名非专业观众,第一次站在这些巨作面前,内心依然存在着疑惑。这个疑惑,曾经有观众在有风君身旁小声地说出来:“看不懂。”
这不怪他,毕竟就连赵无极1985年回国讲学后,也发出过疑问:“我开始怀疑,中国,我的祖国,它有朝一日能理解我的绘画吗?”
但是,第二次的艺术之旅,有懂油画的人为我们讲述赵无极画作的魅力——跟着中国油画学会会长许江看完这场展览,赵无极先生的伟大之处,也能略知一二。
01
走进展厅,苹果静物、在杭州居住的房子……这些画作似乎和抽象并无关系,也正如赵无极曾说过的,“要画好抽象的东西,你一定要有很好的写实功力,从写实到抽象,你的抽象才会有内涵。”

赵无极,《无题(有苹果的静物)》(Sans titre [Nature morte aux pommes]),1935-1936年,布面油画,46 × 61 cm,摄影:Antoine Mercier

赵无极,《我在杭州的家》(Ma maison à Hangzhou),1947年,布面油画,65 × 80.7 cm,版权保留(Reserved rights)
但是继续前进,展厅内的画风陡然一变,无数的青铜铭文、甲骨文从天而降。
这正是蕴藏在赵无极身上的“两个传统”,东方和西方,许江说。
他的艺术汲取中西文化传统,兼容并蓄。他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与书法启蒙,早年入读国立杭州艺专,服膺林风眠、吴大羽先生融合中西的艺术主张,深受印象派以及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绘画的影响。
1948年,赵无极赴法深造。初到巴黎,他的画作仍是对生命记忆的表达。1951年,他在瑞士见到保罗·克利的原作,顿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潜能。他以甲骨文、青铜器铭文为灵感,用想象的书符创造形体,营造空间。

赵无极,《十月伊始》(Début d'octobre),1955年,布面油画,97 × 146 cm,现场拍摄

赵无极,《我父亲的花园》(Jardin de mon père),1955年,布面油画,38 × 46 cm,摄影 © 中国美术学院
那种甲骨文的秘符仿佛被一种火光激活,一种古今贯连、宇宙一体的神秘气息,被幡然点亮。这种漂浮的、古老的悸动,让赵无极从早期绘画中克利的影响中挣脱出来,与东方字符的鬼哭雨粟的奇绝瑰玮相融汇。
这是赵无极艺术创作的第一次重要转变。
我们看到这一极具创造性转化意义的真实过程,西方的艺评界将这一风格叫做“荒碑”系列。这种“荒碑”的郁郁累累的质感,感动了无数中国人。
鲁迅曾说,“木刻运动一方面要像匕首,批判现实,唤起民众,另外一方面要向中国的古碑学,要向中国古碑的刀法的那种荒朴之感学习。”这些文字,像漫天的法器,钢浇铁铸,威威磊磊,笼盖四方。这里边有天地的萧然,有浩瀚的悼怀,有远古的苍茫,有訇然的炸响,令人震撼。
02
进入下一间展厅,也进入了赵无极先生艺术创作的第二次重要转变。
1957年,赵无极在美国旅行时,结识了纽曼、罗斯科等抽象派画家。抽象表现主义扩展了他的绘画视界。1958年起,他不再为作品命名,而是以作品完成的日期命名。
20世纪60年代,他从形象和字符中解脱出来,以表现主义的狂飙涂抹响应草书的笔势与章法,将自己抛入绘画之中。至此,他的创作逐渐演化为一场肉身与画布搏斗的行动,在自发性的书写挥洒中,逐渐生长出山水意象。

赵无极,《09.03.65》,1965年,布面油画,130 × 162 cm
现场拍摄
他在巴黎艺坛的上空,却俯察到一种穿越东西方的山水之象,并开启了他一生最伟大的创造时代。
这也是本次展览当中最精彩的部分。画作中的文字已经解体,转而变成了山水。但和传统绘画不同,和很多人的方法不同的是,赵无极表达的不是山水之象,也不是山水之形,他画的是山水之气,仿佛洞见山水苍茫之中的烟岚之气。
古典油画的语言被用到了最具东方诗意的绘画上,他仿佛捕捉到了天地未分之时的鸿蒙气象,让山水意象化在“气”之中,化在“气”的浑茫流溢、翻转蒸腾之中。在浑茫之气中,他找到了“骨头”,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山水之美。

赵无极画作,现场拍摄
有风君眼中还混沌一片的画作,忽然如盘古分离天地般清晰起来。山水的鸿蒙之气或从天而降、贯穿全网,浩然澎湃,或冲击碰撞,挣脱束缚,肆意生长,或团团环绕,难分难舍……这何尝不是中国山水带来的视觉冲击。
将中西艺术融会共生,正是赵无极的伟大之处。
03
绘画中,又沉淀着多少人生况味。回忆中的赵先生,是一个可爱的人。
2004年,赵无极来访杭州,许江陪他重游西湖畔的罗苑艺专旧址,坐在艺专当年的阳台上,赵无极像孩童般开怀大笑。当天夜里,赵无极到许江的画室看画,他劝许江不要当院长了,还亲自示范了用油的妙意,并承诺为许江买油。一个月后,许江工作室的电话铃响,赵先生在电话的那头吃力地说:“我是无极。”
原来,他在巴黎为许江买了油,调制好,带到邮局,邮局说这是危险品,不让寄!他只好来道歉。
油是小事,却寄予着某种期许。

现场拍摄
而在二楼展厅,一张满是大刷子的照片铺满整面墙,这是赵无极的绘画工具。1985年,在短训班时,赵无极就喜欢用大刷子,当时学生们还想着成立一个“刷子画派”。
不像其他人改起画来,如疾风狂草唰唰唰,赵无极用刷子帮学生改画,果断中带着柔情,就像用清水轻轻地从婴儿的脸蛋和屁股上抚过一样。他的习惯,反映在干净的笔刷和调色盘上,在绘画之外,是一种修为,也是一种境界。
再回头,“向民族的优秀传统学,向世界第一流的大师学,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上自己的个性,这样自然而然地融合起来,形成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不应该是地方性的,而应该是国际性的,世界越来越小,东西方互相渗透,中国画和西画的界限已经不存在,不要找个套子将自己套住,应站得高,站在世界艺术之上。”
赵无极先生的谆谆提醒,仍让我们倍感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