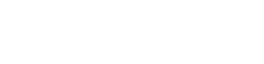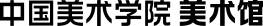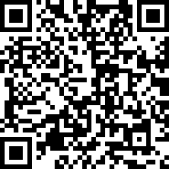无效兑换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青年艺术家扶持项目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承办单位: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基本视觉研究所
学术主持:张培力
展览总监:余旭鸿
策 展 人 :童茜、杨又晨、张钧雷
展览统筹:夏商周、蔡可成
媒体宣传:赵怡、杨翔
视觉设计:杨炳华
参展艺术家:
陈芷豪、傅文超、黄晶莹、龙盼、刘宸、吕凯杰、刘铁源、李心夷、李依珊、林璟、米一峰、Pumunu、潘草原、邱奕雯、施三本、沈蕊兰、石冰、申一涵、王志鹏、汪嘉欣、月台小组、于航、易超、Ziv Zeev Cohen
展览时间:2019年3月26日——2019年4月26日
展览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实验展厅(-1楼)
特别鸣谢:范厉、张辽源、刘畑、郭熙
“无效兑换”是有关艺术作品与观看之间关系的一次提问。是谁在制作可以被观看的对象-作品?他们设置了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被观看”这个问题?又是谁在看,用了什么观看方式在看?他们两者之间可以兑换、能够兑换的是什么?是否存在着有效的兑换,什么阻碍了兑换的产生,什么样的设置才可能建立有效的兑换?或者根本就是无效兑换?
本次展览选择了未被标签化的青年艺术家,以策展人与艺术家的对话代替了展览阐述和作品展签,艺术家的展示不仅注重作品本身,同时要求艺术家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过程、创作状态也呈现在展览中,致力于制造出每位艺术家的“小气候”。
整个展厅由空间本身留存的特殊格局的小空间展开,展览空间保留了原始的状态,并将原有空间特性进一步加以发挥。观众将线性地穿过一个个独立且个性鲜明的艺术家作品区块,转而到达开阔的大空间,观看不同气候在一个平面上的“对流”。这种“气候”和“对流”,正是艺术本身的“不可兑换”的能量。
李 依 珊
李:这系列创作最初是一个小想法,从一个实验开始的。当时我是在涂指甲油,发呆时,突然想到人类真的是不遗余力地寻找身体上每一寸土地进行装饰或改造,其他生物会有怎样相似的行为吗?如果我强行以我的方式对其进行改造会对它们的生存有什么影响?”

李依珊——Viva la Vida 生命万岁
装置
尺寸可变
植物
2018
Q:平时的生活创作中你会经常关注这类型的事情吗?
李:会从自身经历挖掘一些有意思的点,然后在动手实践的过程中可能也会不断加进新的元素,一点点完善自己想法。

Q:人类对自身的装饰是外在的,可是对植物的缝纫是伤害其本身的,这点你怎么思考?
李:我们扎耳洞、刺青、烫发、整形其实也在不断伤害自己,且每个人心里都会有不一样的标准来评估这种伤害。我也在摸索怎样在不伤其根本的前提下在植物上进行创作。

Q:这件作品跟你其他系列的作品有什么联系吗?
李:都是在了解自己的过程中的一些思考吧。跟植物相处以及构思的过程能帮我理清一些繁杂细碎的念头,并让我感觉到一种简单的平和。我之前可是一个连薄荷都养不活的人,这系列的创作也让我看到了不一样的自己。最近在看有关植物进化与分类的书,之后的创作也会与植物相关。
李:这个是我跟朋友一起合作织的,画面里面的形象与事物都是在我们俩生活中不断交叉出现,对我们有深刻影响,生活中不可缺少,或只是带给我们简单的快乐的一些东西。
吕 凯 杰
Q:关于这组摄影,后来为什么会想加入动态视频?视频的内容也是关于夏天吗?在想,为什么你会做这样一件作品。
吕:不是的,因为喜欢日落时候的景象嘛 然后经常会跑去西湖边看日落 ,然后有一天突发奇想。感觉可以开个直播 分享分享 给看不到的人也一起看看。然后 去年夏天时候就开始开直播了在YouTube twitch 还有Instagram上。然后,平时也有拍一些这些景象的照片。后来,积累多了才慢慢说想做一个作品。所以,并没有先后之分,几乎是同步进行。

吕凯杰——hot summer nights
摄影/影像
尺寸可变
2019
夏日的傍晚,更多的只是一个湿答答的 有点粘 光脚走草地上露水沾湿脚踝 的一种意象吧 (啊吖吖 想想就好腻哈哈哈哈哈),可做的东西里更多的其实更夏天没什么关系。
在媒介上也想说是希望能跳出摄影的范畴 用图像来说话。然后就是 平时比较注重一些情绪性的东西,也在试着把情绪变成作品的一部分材料,从而用情绪来搭建一个作品↖(^ω^)↗

Q:直播日落,真的有人看吗?
吕:有人看的,人不是很多,但还是有人好奇点开毕竟其实比起电子竞技这些来直播来说看日落直播是个无聊透顶的事情的事情。不够刺激,23333, 但我自己感觉这个事情还是有一点点浪漫的。
潘 草 原
Q:你为什么会对闪烁或装饰材料有这么强烈的兴趣?
潘:也许是一种本能。翻看自己小时候的画作时,发现会反复出现穿着长裙的公主。 其中公主裙会画的很大,夸张地占据着画纸几乎全部面积,因为公主裙是一个待填充的装饰空间,我热爱变着花样用不同的装饰带来填满裙子,享受这种框架(framing)和装填(filling)这一系列行为带来的愉悦感。

潘草原——闪烁其词
纸本/空间装置
尺寸可变
综合材料
2019
Q:你怎么看类似这样的作品啊?我觉得很好玩。不知道你怎么看。
潘:不是我的菜。
Q:不严肃?
潘:我会把这类作品归到艺术男中年趣味。艺术圈也是被不同趣味划分阵地的,比如我的趣味就是视觉性文学性先入为主,可能你的趣味是概念幽默先行。
Q:这样的呢?
潘:也很艺术中年啊。


Q:你之前做的作品以平面绘画为主,这次更像是一次研究然后生成的作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潘:其实我我本科和硕士专业都是漆艺,这是一门装饰体系庞杂,材料品类诸多的学科。制作漆画的过程就是利用原始材料构造出新形态的过程,使用的材料往往是天然材料(大漆颜料、金、银、贝壳、麻……),一副完成的作品往往是完满的。借着这次展览的机缘我试着扩展材料的范围,除了手工制品外也将现成品、出版物等都纳入自己的材料库中,在手法上更接近编排而不是创造。
黄 晶 莹
Q:你这次展的作品,画框、A4纸和文档,和你之前创作影像的方向和感觉很不一样。为什么会突然做这种类型的作品呢?
黄:为什么忽然做这样的作品:因为我最近开始怀疑我所做的事情,怀疑艺术本身。
我觉得我一直是很矛盾的艺术态度,一方面,我相信艺术本身,所以我会做像之前那种类型的艺术作品,另一方面,我怀疑艺术本身,所以就有了现在这些作品。而对艺术态度的矛盾,也让我开始思考新的作品模式。

黄晶莹——没有就是有
装置
尺寸可变
相框
2019
Q:这么说来,你创作的出发点都是对艺术本身的一些思考呢?是不是和你的生活经历有什么关系呢?
黄:其实也并不全是,我觉得艺术问题的答案不是一下子就有了。或者说对于艺术的疑问也不是一开始就会有的。这是一个摸索的过程和反复思量的过程。和我的生活经历唯一相关的,应该是我性格执拗?
我真的不知道和我生活的关系,感觉似乎是和生活分裂的状态。


申一涵&汪嘉欣
Q:不如简单聊一下你们这次的创作?
申一涵&汪嘉欣:这次展览的合作挺逗的,作为两个对于影像处理有不同方式的人,在基于对一个通道的臆想,组织大量网络视频,在理解说明书、广告这种通俗媒体的组织语言后,揉杂在一起,做了一个关于空间传送的作品。这些网络视频基本上都是边组织边曲解的状态,编造空间传送在当代生活当中无所不在的证据。

申一涵 汪嘉欣——空间传送的家庭范式
尺寸可变
双频影像
8’35”
2018
Q:这一次,你们为什么会选择去联合创作?
申一涵&汪嘉欣:出发点源于我俩对于钻进这个空间的体验感非常好,本来以为通道只是一个完全封闭的底部,但是里面有两三人高的空间,头顶盘旋排风扇。钻进这个通道能够在某种程度上体会一种惊叹,尤其在我们俩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我们有请观众进入的意愿,但我们希望将我们第一次的那种体验瓦解。在我们竭力消费这条通道之后,他被赋予了丰富的解释,但却唯独不传达惊叹。


沈 蕊 兰
Q:“消失”创作的契机是?
沈:其实是基于当时开始对“语言的功能”产生了怀疑。语言的边界在哪里。语言是否可以指代一切事物,包括感受之类的。以及词语、符号与它们所指代的真实事物之间的距离。这个小说中的人物因为一场视觉的畸变逐渐开始用介词写作,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语义的消解。最后把自己的存在也消解了。
在与你聊之前,已经有点忘记当时创作的原因。现在终于稍微想起一些。当时做的笔记,现在也已经看不懂。

沈蕊兰——当一切光都熄灭
单频影像
尺寸可变
5’38”
2019
Q:你遗忘了自己为什么做这个作品显得很切题,记忆消失在了创作之中。
沈:并且小说第一句话就是:“本来,我完全不记得这个人。”希望观众也是看完就能忘掉。现在做成书是因为与一个设计师朋友探讨的时候说怎么把这个主角的那种感官体验放到书的本身,继而发展成现在。


Q:这样消失的感觉似乎也在“当一切光都熄灭”这个作品里出现?
沈:你是说视线的消失吗?其实我做这个作品的时候没想到消失,这个影像一开始是来源于我个人的阅读体验。

Q:消失其实也和文字有关,阅读似乎成了你的生活常态。
沈:看完书后会留下的印象和感受不完全书里的文字所指的东西,我经常走神。
我对日常生活里面的异化的东西很有兴趣。感觉这些东西和想象力是有关的,尤其喜欢阴翳美学,就是事物处在半明半昧的那种状态。有段时间喜欢晚上出来闲逛。
Q:你在暗夜里奔跑的状态?
沈:不是全黑的地方!全黑就太阴暗了。
我在看一个我非常喜欢的台湾小说家骆以军的《西夏旅馆》时,它里面有和文明、历史这些宏大命题的相关的部分,也有那种细枝末节的个人感受。我去回忆我的阅读体验的时候,会发现小说的语言会隐隐留下一个印象在那里,成为一个个人经验的东西。有时候这种印象是毁灭式的,可以摧毁你在被教育的过程中对一些事物的概念上的片面理解,就是文字所制造的那种记忆,那种庞大的幻觉一样的东西,好像根植在每个人的原始生命力,然后通过阅读,这种东西就被唤醒了。这个录像就像是在模拟这一个过程。
沈:总觉这个世界还是需要秘密,所以就做创作。

Q:创作是秘密?
沈:不是,就是说这个世界需要未知的东西。如果想知道真理,就去做哲学家和科学家或者出家。
Q:所以这些作品创作都是关于一些未知的存在。
沈:关于如何感知未知。我自己就是本来对这些很麻木,通过做东西有时候会突然觉得好像和这个世界多一些联系。

Q:是这样,做作品会让人变得敏感起来。
沈:对。“一些时刻,夜晚在黎明前终止”其实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些,由夜游开始的项目,而且还没做完。
这个项目始于夜游。有段时间我总是在夜里,在杭州的不同地方步行闲逛。这可能是一种用身体丈量地理的方式,就是你对这个城市的理解会在你整个闲逛的过程逐渐深入。在这个个过程中我有遇到一些奇异的事情,会和一些很神秘的东西擦肩而过。我觉得的去理解一个城市不太需要去百度或者什么的,就是去在这个环境里闲逛,不一定非得是明亮的地方,有时候可以是这个城市的暗面。所以我也喜欢拍纪录片。我拍了大量有关夜里的茂盛植物,在那个蓝色的屏里文字“一些时刻,夜晚在黎明前终止”的背景里有呈现。然后我又把这些植物投射到一些日常生活的环境中,比如夜里偶尔有人经过的站台上,晾衣服的天台等。这些影像很像是一种来自远古的幻觉,他形状上不是很具体,也没有说要去表达或者呈现什么。
施 鑫
Q:这次的两个作品呈现方式都挺特别的,是不是在展呈方面有特别的考虑?
施:“浴室” 这个作品是空间与时间的错位不断交叠而成的。浴室本身是一个非常私密的空间,作品中人们在此交叠喧闹如同公共场合一般。这种冲突感延续到这次的展示中来:利用楼梯口的正负空间分屏展示,一个屏幕是人们在篝火前长谈,另外一个屏幕是“浴室”这个作品主体。公共性与私密性就此碰撞,来了一场包裹着风情的爆发。
 施鑫——Flow
施鑫——Flow
单屏动画
尺寸可变
05’00”
2018
“flow”笨拙的用了一席帘子和狭长的隔板墙,其本质在于“凝视”。我相信大家都有通过狭窄巷子的经历,目光会锁定尽头的那道光,这个展示非常具有情景式体验。“当你在凝视作品的时候作品也在回望你”,作品中的人物的交流并非电影镜头中惯用的“正反打”手法,而是时常面向镜头或者是说面向观众。而阅读台上展示影像是从正片中提炼甚至是延展开来的,我试图让观众在碎片化的影像中游走,自行构建起其中的联系。


Q:为什么会选择动画的手段来做创作?
施:这可能来与最初的训练有关。我在幼儿园时期因兴趣开始接触绘画,在长达十几年的绘画训练中,它已然成为我的肌肉记忆了。再则,我的创作启蒙是一个叫“一米剧场”的课程训练,你会被限制在一个以自身为圆心半径一米的狭小空间里进行影像创作,同时创作密度非常之高且须“零成本”,这种极端的训练下会激发出很多意想不到的奇招。

拿“浴室”来说,重叠编排的特殊叙事结构若采用实拍,会涉及到大量的人员调度和道具制作,这对短期的创作实施来说是不现实的,动画这一媒介恰恰充分发挥了优势,虽然它占用了绝大部分的时间。而“flow”大量涉及了对自身记忆的追溯和再创作,除了镜头可以让它们穿过时空的长河之外,再来就是画笔。肆意妄为的想象不被实施的问题禁锢,与其说是选择,不如说是被选择。
石 冰




Q:你的创作过程中有很多不同的方向 ,甚至是感到一种分裂在里面 ,你怎么看这些分裂的产生 ?
石:可能是受到德勒兹的影响,我开始放弃或不在意所谓的系列性和统一的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系列性和统一的面貌是一种“无可奈何”,一种被系统规训的状态。我开始放纵我的分裂状态,试图通过最大限度地分化来实现一种新鲜感,确保一种敏感和创造的活力,当然,我现在也越来越随性了,可能分裂也是我本能的考虑。


Q:你的这部分参展作品,其实对于观众并不是很好被解读,你怎么看这种观众与艺术家对作品解读得差异性?
石:我觉得这次的展览作品本身没有什么很深刻的含义,它的意义就是所见的事物。而且,这次的作品也不是作品,因为有些基本上并没有做完,我将这些事物贯穿在我的日常和我的个人时间里,和其他人没有关系,可以说是非常闭合的,我是在和自己对话并讨论自己的问题。另外,当我开始放大自我时是否说明了“我”的重要性,我想也不是,我反而认同福柯的思想——并不存在作为作者的主体,作者在表达后消逝。我认同作品本身,或经行动遗留的过程本身即可说明这个世界,“我”仅是一个导体,观者或阅读者会从作品本身遭遇他们自己的世界,且又是差异化的。
学校会考虑学科的纯正性,在某些传统专业中似乎必须得这样,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遇见这样的问题。
我以前的专业会存在这个问题,但是现在还是主要看创作本身,前提应该是创作本身不是材料。


石:包括像张老师,很多时候你在这个展厅看到的作品,换到下一个展览面目就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在北京,哪里的艺术家似乎展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面貌,或是一种风格和态度吧,但这样确实好吗?有的时候看张老师的作品我都不知道这个是张老师做的,这样似乎也很好。
易 超



Q:当时在铜场看到你们的展览《公园计划》,觉得你们做的感觉很猛。那个展览你们花了多久时间才决定那么去做的?还是突然有个灵感就开始动手准备了?
易:构思,收集,制作到展览前后两个月吧,冲动开始的工作。不是突然有了灵感,是之前对这方面有过关注。然后对这种制作方式感兴趣。
Q:你们做作品有些特点就是很直接,很有体量。有些朋友会开玩笑说你们都是“直男癌作品”。
易:这种直接我觉得是建立在材料和材料来源整个链条之上的。
Q:你还有一部分作品感觉都和重复劳动有关系,还有一种比较克制的感觉在。就是黑色那部分作品。这次展览还有两个艺术家都在作品里涉及到这个话题。(石冰,还有傅文超的作品。)就我的感觉这和无效兑换这个主题也有某种联系。这种大家看似无效的行为被放大后,其实也形成了一种有效的表达,不知道你是怎么理解你的这种看似无效的重复劳动的?
易:我觉得一些无用的行为或者是无效的事件,最终回到了人的身上。很多东西看似和我们息息相关,但在线索的指向上却不是我们。


傅文超


Q:在你的作品里我个人感觉会有一些比较克制的情感,总是会出现很多的重复劳动的内容,这是你的性格让你不知不觉的出现这样的特征在作品里,还是漆的这个材料带给你这种感觉?
傅: 两方面都有吧,我理解“重复”有两个方面,一种是米勒在《小说与重复》中提到的“重复观”,这是积极的,向上的,提倡用“重复观”解决难题。另外一种是比较消极的,被迫的“重复”,就像很多上班族一样,所谓朝九晚五,不过是不停的重复,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让自己舒服。而后一种是我很怕出现在自己身上的,也是我所思考的。当然,大漆这个材料也会带给我这种感觉。

Q:你也是通过裱布这个行为在里面转化这两种感受吧?平时你喜欢收藏一些老物件,你觉得这对你的创作有启发吗?
傅:裱布呢,是大漆制作里的一道工序,它只在制作特别东西中才会重复操作,我把它提取出来,重复裱布的动作,思考这个问题,思考重复的力量,当然也思考重复带来的安逸。
启发当然是有的,我很喜欢老东西,所以有相当一部分作品与之有关,说的冠冕堂皇一点,收了老东西,因为喜欢,那得了解它吧,那么年代呀,材质呀,文化呀,历史呀,审美呀,这些都会去了解,这些就是知识吧。通过把看似无效的这个行为放大后其实也兑换出了一种有效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