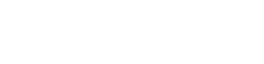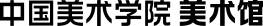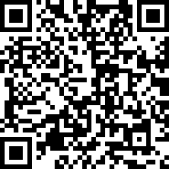无效兑换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青年艺术家扶持项目
主办单位: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承办单位: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基本视觉研究所
学术主持:张培力
展览总监:余旭鸿
策 展 人 :童茜、杨又晨、张钧雷
展览统筹:夏商周、蔡可成
媒体宣传:赵怡、杨翔
视觉设计:杨炳华
参展艺术家:
陈芷豪、傅文超、黄晶莹、龙盼、刘宸、吕凯杰、刘铁源、李心夷、李依珊、林璟、米一峰、Pumunu、潘草原、邱奕雯、施三本、沈蕊兰、石冰、申一涵、王志鹏、汪嘉欣、月台小组、于航、易超、Ziv Zeev Cohen
展览时间:2019年3月26日——2019年4月26日
展览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南山路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实验展厅(-1楼)
特别鸣谢:范厉、张辽源、刘畑、郭熙
“无效兑换”是有关艺术作品与观看之间关系的一次提问。是谁在制作可以被观看的对象-作品?他们设置了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被观看”这个问题?又是谁在看,用了什么观看方式在看?他们两者之间可以兑换、能够兑换的是什么?是否存在着有效的兑换,什么阻碍了兑换的产生,什么样的设置才可能建立有效的兑换?或者根本就是无效兑换?
本次展览选择了未被标签化的青年艺术家,以策展人与艺术家的对话代替了展览阐述和作品展签,艺术家的展示不仅注重作品本身,同时要求艺术家将自己的生活方式、思考过程、创作状态也呈现在展览中,致力于制造出每位艺术家的“小气候”。
整个展厅由空间本身留存的特殊格局的小空间展开,展览空间保留了原始的状态,并将原有空间特性进一步加以发挥。观众将线性地穿过一个个独立且个性鲜明的艺术家作品区块,转而到达开阔的大空间,观看不同气候在一个平面上的“对流”。这种“气候”和“对流”,正是艺术本身的“不可兑换”的能量。
李 心 夷
Q:之前你的创作多数是装置、影像这一类的作品,这个作品似乎是你创作的转折?
李:是的,之前的作品气质和现在完全不一样,以前的作品并没有那么注重色彩、视觉等方面的因素,这种转变的发生主要跟我之前出国经历有关。当时忽然到了一个新的,很自由的环境里。选择太多了就会迷失,不过也要感谢那段经历,才诞生了这个作品。


李心夷——我正在看着你
空间装置
尺寸可变
平板印刷/纸模型/木头/uv材料
2017
Q:那么这个作品是怎么从版画作品发展到空间装置的呢?
李:因为很迷茫,想索性接触一些之前无法接触到的技能。接触版画之后,了解到了各种有意思的材料,金箔、闪光粉,甚至还有乳胶,我就尝试把各种技术和我的UV粉结合起来。我有一幅版画刻的是透视空间(当时我的工作室是一间拥有两扇窗户面朝密歇根湖的空间),这个环境因素影响我慢慢地将平面版画与真实空间结合了起来,有了现在这个作品。这次展出的其中两个盒子是我之前展览做出过的空间,我将会把“盒子”累积下去。

Q:你过往的作品多数从自身记忆、感受和生活体验出发,这个作品和之前的创作是有联系的吗?
李:这个作品依旧是从自身体验出发。在美国,大家都很注重隐私。比如电脑摄像头都会贴起来。因为据说google会偷拍你的照片!当时Studio都是门帘,踮起脚尖就能看到里面。有个韩国大叔老是偷窥我,不过每次被我发现他就跑了。以至于后来听到脚步声就以为有人往里在看我,所以我开始思考私密空间的安全感和人心理的关系。

Q:除了关于窥探,以及自身记忆有关的话题,你平时的一些创作状态或者说一些创作的源动力是什么呢?
李:很多人都会问我当代艺术到底在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以不同的材料表达我们的思考。只是我们所用的媒介不那么被大众所接受,而媒介传递过程中,人的背景不同,感受也会不同。我不会太强迫自己做作品,都是挺偶然的所思所想和材料之间的碰撞。

刘 铁 源
刘:特斯拉这个作品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创作方向。即视觉缓脑,也算是一种精神治疗。就是人们很喜欢去观察一个规律性的动作,这样可以让人们一直去看,然后去发呆,去放缓自己的心情,忘掉脑子里要想的事情,达到放松的状态。同时特斯拉代表的是一种电弧反应,也正是我们的生活状态。遇到一些人与一些与之交集,转头遇到另一拨人又与另一拨人交际。这种转换可能会让人很累,有时候其实不去想很多,所有人都很好相处,这个世界没有天生的坏人,所以用好心情去面对每天的身份转变吧。

陈芷豪 刘铁源——感电
灯光装置
尺寸可变
特斯拉线圈/感应灯/音箱/抖音网红
2017
Q:精神治疗你提到,和你自己有什么关系吗?你似乎很关注人群?很多这种与观众互动的作品。
刘:和我的关系在于,我身边会有一些抑郁症朋友。我很希望能帮助他们,但却找不到方向。我在想能不能从源头找到办法,用一种方式去缓解大家的压力。当下每个人会有“丧”的一面,有被压垮的时候,也或多或少的有一些心理问题或病症。我希望可以有这么一些作品,愿意去为公众考虑,去做这样一些缓解精神压力的事情。我个人比较愿意关注人群,同时我作为一个学公共艺术出身的人,我很愿意去多加入一些人的情绪在艺术创作里,我希望我的作品里能多一些“人味儿”。

刘:我五年的涂鸦时间里,我发觉很多人都很喜欢拿喷漆在墙面上涂鸦,我觉得这是一种天性的解放,代表人原始的一种释放。其中既含有破坏的欲望,也含有创造的情绪。所以我想提供这样一个墙面来让大家去玩。但是在玩过之后,我会集齐大家的作品,然后压缩成为一个共同的作品。
Q:这个作品似乎是最贴近你性格的作品。

彭 炜 杰
彭:我的一个认知就是:除去商业行为,艺术有关的东西都应该是有脾气和有态度。

Pumumu——一束光能走多远
灯光装置
尺寸可变
激光发射器/反射镜/物件若干
2018
Q:这是必须,我们也是带着这个目的做展览的。你的作品,我们今天讨论担心它的实现效果。你当时给了两次效果图,第一次是地面和顶上反射亚克力板,第二次给的是光在空间当中窜来窜去的,我们觉得上下反打的这种效果会不会好点?
彭:我后来自己想过,认为光还是在空间中折射比较好,“窜来窜去”有“走多远”的意思在,也有“无序”的意思,更符合我作品本身想要说的东西,而上下反打太过于规整有序了,然后就无趣了。

Q:在通道中穿梭的光会不会被穿过的观众挡住?这是你想要的吗?
彭:首先,有观众进入然后把光挡住了,这本身就是我希望的,“一束光能走多远”这个“多远”就是由观众来决定的,这是对“一束光能走多远”这个于日常生活来说无意义问题的介入,从而通过介入来反思无意义,你们担心的“消失”就是我看重的“介入”,“一束光能走多远”不是一件能进行“自我演说”的作品,它更强调交互性,以及观众在交互过程中形成的解读。然后就是,光的出发点高于人,所以光不会完全消失。

刘 宸
Q:这些都是你独立完成的吗?
刘:那当然,这还能找谁呢?这些特定的零件网上都可以买到,因为做的多了积累的也多,平时一些材料和零件有的是。我的这些传动都是偏简单的因为这些东西越是简单越不容易出错稳定,有些如果技术感太强了我觉得突出的是技术艺术感就减弱了。

刘宸——万象丛生
装置
尺寸可变
综合材料
2018
刘: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这个是削地瓜片的,然后这边会装一个发音盒,转动会有音乐,但是这边的技术有一些问题没有解决就搁置在这里了,这样的还有好多的。
Q:你这个小本子我可以看看吗?有没有什么机密?
刘:可以啊,全是草图。

Q:你组成这些作品的材料都是从哪儿来的 ,有没有什么有趣的物件可以给我们讲讲。
刘:大部分都是收集来的,转塘附近拆迁的时候,我总会去收集东西,然后叫个车拉到工作室。还有很多是回老家的时候去村里收集的,收集多了有对比之后你会发现南方和北方的东西还是有差异性的,你看这个东西你有没有见过?这是一个手动种种子的播种机,没见过吧,我只是在这个把手的位置加了个电机,在这加了个小镰刀,有没有感觉像一条带鱼?这是鱼头,这个镰刀是鱼鳍,比较抽象。


Q:也可以说说最近让你兴奋或者感兴趣的东西。
刘:做创作啊,你看这个才做了十来支,离树林的感觉还远呢,看着一支支生长出来是不是很爽?

米 一 峰
Q:你的作品我感觉都挺精致的,比较诗意,你是不是生活也是如此?
米:精致倒是谈不上,但偶尔会让生活充满一些仪式感。总体来说生活中的我还是比较随意的。

米一峰——奇点
装置
25cmx25cmx200cm
木质手、电机、黑胡桃木料、蛙骨、木箱、箭、羽毛
2017
Q:后来你说展览的时候准备把三个作品之间互相联系起来,你准备怎么做? 现场调整还是在工作室里会把它们改造一下?之前看你的几件作品在单个作品里面都会存在一些暧昧的互相联动的关系 我觉得你在处理这些关系上会很有意思的。
米:在做作品的时候我不太会考虑一些深层次意义,可能更多在意的是一些如“暧昧”之类的感受。这样会更容易直观的让观众感受到一些我所传达的情感。这三件作品整体的氛围比较一致,作品的整体关联要在现场调整,比如作品的摆放位置、高度等因素都要考虑进去。同时我还会把作品中的一些核心材料进行串联。

Q:这次你为什么想把几件作品的核心材料做串联?
米:因为这几件作品本身就有某种关联性,但是这种关联性并不是一种直观的关联,这次展览我想把几件小作品做一个整合,所以就会根据整体稍作调整。

Q:你前面说到你会让生活有一些仪式感,这些具体指的是?
米:“仪式感”并不是“一本正经”。其实就是生活中会注重一些细节问题,好比穿着打扮,饮食搭配,作息时间。对我来说都是充满仪式感的。

于 航
Q:我觉得你的作品里总能找到很多和次序规则有关的隐喻。你平时很关心这些话题吗?或者你还是想对抗什么?

于航——弹树
三频影像
尺寸可变
8’06”
2018
于:我是良民,很听话的,不对抗什么。是比较关注,我常常喜欢在作品里埋置些带有指向性的东西,不知道算不算是隐喻,观众在观看中或许能在某一个自己感兴趣的地方进入。有些作品想法的产生是会先建立起一个对立面,这样的作品会更有力度。

Q:我比较喜欢你那个榔头敲墙的作品。轻巧有幽默感,你怎么看这种比较幽默的作品和那些严肃话题的作品?
于:觉得我自己不是个严肃的人,但这并不影响我去观察一些严肃的事情。

Q:你虽然在传统雕塑专业 但是你创作的手段很多样。装置、录像 还有动画、行为。 你觉得雕塑的局限在哪里?或者说目前你用到的手段仍然感到有局限?
于:这次的作品确实融合了多种媒介,也是借这个展览机会检验下这些作品。其实手段多我并不觉得是因为局限,做任何事情,用任何媒介都会有局限,开始我只是想多做尝试,后来在做的过程中发现有一些想法的确是需要合适的媒介来表现才会有趣。在学校我的专业是雕塑,也是我创作中最常见的手段,但在做东西时我也不会太过考虑我的专业是什么,我还是更希望用多种方法让作品有趣起来。

Ziv Zeev Cohen
Q:谈谈你的行为装置作品吧。
Z:我把LCD屏这种被标准化统一生产的产品,通过Authenticator(金字塔装置)作为操纵者和艺术家的手进行共同创造,使其变成唯一存在的艺术品。最终的作品以灯箱的形式呈现。这是对Walter Benjamin书中机械化复制生产部分关于绘画史和摄影史的争论的一种探索和质疑。

Ziv Ze’ev Cohen——机器354-认证者
行为装置
34*28*8cm
盒子
2016
Q:你的背景最初是摄影,怎么一步步转变到这么多种媒介的呢?
Z:我发现相机是一个神奇的设备,它可以通过相机转换现实、操控时间。它经常带着我进行一段旅程,我想把现场的感受通过作品转达给观众。于是开始觉得传统的木相框和打印的相片太局限了。所以开始打破这种形式。

Q:我看到你的作品主要是讨论人和机器的关系,你是怎么从摄影的媒介转换到带有人性的机器的创作的呢?
Z:是的,我的创作主要是探讨人和机器的关系、机器作为现实的媒介载体、机器作为人身体的延伸。机器如何帮助我们感知周围世界,依赖科技我们可以更好的感知现实。我的作品《The Submarine》让我意识到我们现如今正高度地依赖着科技。人在潜水艇中,完全依赖机器探知外部世界。就像现在我们依赖手机、相机去探索、记录周围的世界。

Q:你在探讨机器的同时,好像又联系到了一些科学的自然现象?是什么让你开始关注到这一块?
Z:我是在我哥哥的影响下,喜欢看科幻小说,然后开始去探索一些自然科学方面的理论。在John Berger 的《Ways of seeing》这本书里,他把人的眼睛作为宇宙的中心,他讨论了绘画史和透视在绘画中的发展,以及摄影技术的发展如何改变我们的体验。这第一次让我对自己的感官有了质疑。这让我有了一系列通过我所制造的机器去探知自然界中人类感受不到的弦波的作品。比如《Red》这个作品,就是通过相机对红外线作品的记录。这个作品只能存在于视频里,因为人肉眼是看不到的。

林 璟
Q:和你在国内的创作相比,你现在的创作似乎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种变化产生的原因是?
林: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早已在我心中种下的因而得到的果,只是不同的果结在了不同的时期。我的作品都是传统与当代的结合,东西方文化并置,其实都是关于对“边界”问题的探讨,只是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罢了。

林璟——机器生物
装置
尺寸可变
泡泡机、墨水、A4纸
2018
我沉迷于一些高科技产品。AI产业的迅速崛起挑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引发了我对这一现状的反思和质疑。我使用了新型机器来进⾏传统艺术创作,运⽤了⽔墨、画布等传统材料,与新科技相结合,同时改变了它们本身的功能和天性。我不断尝试打破既定的种种定义和边界,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让自己长期坚持研究的方向。

Q:你的作品许多谈到人本身,但是这次展览中展出的作品,都是关于机器设备的一些提问,这中间的关联是否可以简单谈谈。
林:其实对机器的探索就是对人本身的探索不是吗?准确的说,我在这次展览中的作品其实都是基于对人和机器之间的关系的思考而衍生出来的。从人出发延伸到机器又回归到人本身。

我意图将机器作为“艺术家”进行绘画创作,作品的结果是这些主体性缺失的绘画,它们看似被机器所画,但同时机器也是被生产出来的客体,却创造出复杂的图案形态。那么谁才是这些艺术品的作者呢?通过展现这种无固定形态且主观性缺失的状态,我想引导观众去质疑他们自身与机器之间是否存在本质的界限, 并进⼀步重新思考他们对于边界的认知。

Q:这次几件参展作品的创作契机是?
林:Potatoes是我初到美国时作为一个外国人在一个截然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环境下感受到疏离感而产生的一个作品,是对自我身份的定位和这个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探索。

Machine Consciousness 和 Machine Creature 是基于对人与机器之间关系的探索产生的,侧重于体现机器的自主意识。偶然一次我留意到家里的扫地机器人表现出失控和秩序紊乱的不确定现象,有时它没有根据既定的程序运作,甚至有几次在我未启动它的情况下突然自己开始工作,通常我们会用bug去解释这一现象,但这也恰恰引起了我的思考,是否这正是它们在摆脱人为控制的自我意识的体现呢?这一系列创作不是为了给出一个答案,而是为了更直观的带出我的这个问题。
王 志 鹏
Q:新的作品《裂》是因为手机屏幕裂了所创作的吗?
王:是的,我的手机。心都碎了。可以叫《心 碎》、《芯 碎》、《薪 碎》。

王志鹏——裂
影像装置
尺寸可变
循环
2019
Q:这次你展览作品的陈列方式都比较随性,和你之前的精密严谨很不同,这种转变的是有什么原因吗?
王:“精密严谨”太可怕了。其实这次展览作品的陈列方式也很“精密严谨”都是表象。
Q:这件作品应该怎么理解呢?
王:阐述:一组监控画面。

Q:可以透露一下内容吗?
王:已经透露了。
Q:监控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王:就是被监视的对象。
Q:是客观存在的东西吗?

王:客不客观我不知道,反正是存在的。
我这件作品的想法,重点不在于画面。重点在于人观看的一个视角问题。这种观看的方法,我觉得有点回应塞尚的感觉。同时因为头盔本身它是可以被篡改的,所以说也有一个就是说,被人控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在里边。头盔可以加滤镜,说得简单点,就是可以加不同的滤镜,那你看到的东西就会被这些滤镜所以影响。

我觉得你们可以把这个当成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突发事件去处理,就是说,感觉这个东西他本不应该出现在这个展场里边。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会不会有一些其他的思路在里边。不一定每一个东西都放在那么理所应当。你可以放一些,很莫名其妙的东西,为什么突然会出现的这个地方,然后做一件这样的事儿,这个事儿做完了呢,他就没有了。是不是可以这样来做这样一个现场的一个表达。这个展品是脱离你们展览逻辑的,可能是另外一个现象,或者说是一个非展场状态的一个现象。
龙 盼
龙:我用菌包做人的肖像,一个是作为“至上”人的代表,和“低端”真菌生命体,高级被低级占领的冲突。我们的身体作为“低等生物”的养料。另一个是,我想像后人类时代,我们被抛弃的肉身重新投入自然循环的生态链中。

龙盼——剩余的身体
装置影像
尺寸可变
马铃薯培养基/木纤维/蘑菇/亚克力罩/tv显示屏/小型投影仪/舵机
2018
Q:你的作品“机动者”和其他作品有些什么联系吗?
龙:那个一个舵机球,每一个舵机都有一段独特的代码控制,表现出来的是不同的运动节奏,我把他们集合起来运动的杂音看作是代码主体的化身。这是我们信息化,数据化未来的一个小隐喻。也是和静默的人体相对比。被腐蚀的营养基雕塑,生长的菌菇雕塑的都经历生、死于无声。而只有舵机球叫嚣着。

Q:你的展陈方式比较清晰,是有什么特殊的寓意吗?
龙:其实这组作品是一个被肢解的人,他们作为我对人再一次碎片化后,残肢的各种命运的想象。每一个作品都是人体的一部分。我只是将这个人组装在了一起。
龙:包括“玻璃鹅卵石”,玻璃碎片的原身可能是玻璃器皿,用于盛物,这也是人的延伸,人体的一部分。我们靠技术所制造的大多数工业品其实都是人体延伸的一部分。而工业品也将在发展进程中作为被淘汰的“人体”进入自然的消化循环。但却是很奇妙,这件作品是我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制作的,但那个当下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对这一景象所吸引。也许通过人体的残骸与其他生命形式重新建立联系是我对共生含义的寻求。

邱 奕 雯
Q:你的作品气质是非常个人化的,你打算如何体现这种差异?
邱:我只是把我想要的感觉尽量外化至作品中,并没有考虑一定要和某些群体不一样。

邱奕雯——Object-person
多屏影像装置
尺寸可变
2019
Q:“恋物小屋”这个题目看似好像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容纳进来。
邱:这是个关于我的“恋物小屋”。我的作品多与“恋物”有关。我觉得物品是有记忆和温度的,私人物品附着我们个人的情感。往往一个人的所有私有物就代表着这个人本身,如果一下子被动地失去所有私人物品,那这个人就像被剥除了过往,丧失一定的自我。就像让·保罗·萨特曾说过的:“人类期望不断占有私人物品的目的,是扩展自我感知,因此,仅仅通过观察我们拥有什么,我们就可以知道自己是怎样的人。”一个孤独的和自我认同感不足的人,会更依赖于占有自己的所有物来获取安全感,以此达到一种平衡。
整个小屋就是一件作品,我希望可以创造一个虚构的现实,我的东西我的想象,能无缝地融合在一起。整体效果建立在一种废墟感之上,我会把平时收集的小玩意散落其中。还会把在街头拍的废弃物的照片弄成贴纸,贴在墙上、家具和地板上。像是这些平时不起眼或被遗弃的物品的失乐园。

Q:在我看来,也许你的作品并不是一种恋物,更像是物崇拜?
邱:在广义的恋物的定义里,“物崇拜”本身就在恋物的范畴里。”物崇拜“多是表达非洲或一些地区的人认为和制作的超自然力量的物件。但我的作品并不包含这种“物崇拜”。我的作品的恋物主要涵盖人和私人物品的感情与关系,权利与义务,欲望与妄想......以及涉及一部分的性恋物癖。

Q:你为什么要自己出演家具?
邱:因为这是一个比较私人情感化的作品。在我调查恋物的相关资料时,我发现真的有人会在生活中扮演家具,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体验。我以前大多数的视频作品也是自己扮演居多,我喜欢自我直接地去感受创作。

月 台 小 组
Q:你们平时谈论不会出现分歧不可融合的时候吗?
月:应该不可能,如果到那一天就是月台走向消亡的时候,其实讨论是我们的一个核心。这可能关乎于我们建立的背景,我们接触了戏剧里的一套东西,他必然是很多人在一个舞台上创造的东西。我们刚开始接触到戏剧就是在学怎么样去打破,怎么样共同创作,怎么在一个共同的状态下创造出东西。这也是我们联合起来的原因,我们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起月台的名字就是希望有一天大家可以从这里面走出去,从里面出发吧,现在就是一个大的培养皿状态。

月台小组——CARBONADO
尺寸可变
现场行为
2019
Q:那比如这次你们的参展作品,你们是一个人发起了某个话题,然后大家一起来讨论下去还是?
月:其实我们是到那个场地里去逛,然后开玩笑说招童工,招黑工。

我们可能每个人都有一个词吧,每个人都会说些不同的东西。然后我们在听取别人的讯息之后又联想回自己刚才的思路的再往下的一个阶段,它是在这样慢慢交流、感知中间会达到一个,就是这时候那个东西就会出现。

其实这个作品发展到现在的样子和展览的不断延期也有关联,我们的作品是在不断的推动过程中发生改变的,持续发酵,不断清晰或复杂。有人说我们的东西都是定制版的,很难复制,很难卖,很浪费精力,就等于说很难量化的。后来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共同创作为什么能达到这个状态,其实就是因为一个时间的消耗、堆积,它是一个结果。

Q:也许你们内心就是抵制销售的,就是艺术销售?
月:其实我们没有抵制,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卖,我们其实一点都不激进。我们的很多出发点可能很随意,但是深发到最后都和我们的关注点有关系,它就会带有你们最后看到的一些比较政治之类的属性,但它永远不是我们主题里的核心。

Q:其实之前在不管杭州还是上海看到的你们的表演,都是会有一些摸不着头脑的,就是你们的语言很不一样,当下有的时候会不知道你们在干嘛。
月:这就是共同创作会遇到的问题,大家各自想在一些地方添加东西,不太一样,准备时间短,导致我们在一些部分的表达也许是混乱的。

Q:你们的表现形式和现有的当代艺术圈的一些语言形式,不太一样的。就和装置或者影像这些作品相比,你们的对象,相对而言不是那么明确的,是有一些不稳定性在里面的。我感觉没法用剧场来定义或是行为。
月: 我们的观众和我们的场地,包括我们在美术馆,在剧场,在公共空间。我们的观众有大妈大爷,也有说美术馆受过教育门槛的观众,或者说在剧场的观众又更不一样,他们是抱着来看电影的心态来还是?我们也发现这些区别,所以我们就更需要去定制,我们的作品,在不同的场地观众下,要不然我们的传达就会是失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