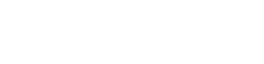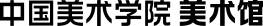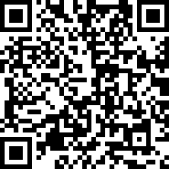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2017年3月,王公懿在“西湖志:王公懿、严善錞作品展”开幕式现场致感谢辞
71岁的王公懿银发飘飞,不施粉黛,脚踩运动鞋,如侠客般健步如飞。
“我这辈子太幸运了,就这么傻呵呵的,老有好人相助。”王公懿爱笑,一笑俩酒窝,说话中气十足,激动时还会手舞足蹈,十足性情中人。她爱和年轻人聊天,但绝不倚老卖老,而是以十足的诚意交谈,“我碰到的都是欣赏楞人的人。”所以她敢言,如孩童般真诚,故不见暮气,相反生气满满,如同一枚元气少女,活得坦坦荡荡,因为她的生活就是这样,“你的生活在哪里,你就做哪里”。
当然,此时的释然并不代表过去无痛,看似风淡云轻,可唯有类似经历的人才会理解期间的潇洒之功。王公懿18岁的时候就挨过整,“同学们有一年没有和我说话。”80年代,因为女性的倔强悲慨和对时代的悲愤,她在老美院的楼梯间里哭着刻《秋瑾》;90年代,目睹国外艺术世界的繁华后对比彼时故园的忧伤,她忍不住在法国当街恸哭;90年代末,从法国带回一批石版画满怀欣喜地办展,没想到骂声一片,“莫朴先生气死了,我特意跑到他家里去请罪。他说你这么有才华的人怎么做这样的垃圾。”但王公懿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特明白,“这不是我的错,也不是大家的错。”有批评非常正常,“但我丝毫不接受,并不是说我和他们是敌人,就是因为大家在不同的时间和方位。”
多年后谈起当时,王公懿笑着总结:“这一生我都感觉很多事情是逆向着来,然后最后的结果是正面的。”

▲2013年,王公懿在浙江美术馆作品展开幕式现场致感谢辞

▲工作状态中的王公懿
1946年,王公懿出生于中国天津,在中学美术组学了9个月后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1966年央美附中毕业,1974年分配到出版社工作,1978年考上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研究生,1980年毕业留校,1986年受法国文化部邀请赴法考察艺术与艺术教育并参加展览,1992年因为系里让她接管石版工作室,去法国进修石版画,两年半后回来,1999年去美国俄勒冈州立大学美术馆做驻馆艺术家,留在那儿直到现在。
上世纪80年代初,她以一套《秋瑾组画》名贯中国,这套木刻重建了中国美术学院版画在新时期的高度,又开创了中国文化传统活化的秉志取向。此后,王公懿以奔放的艺术个性行走天涯,创作了浩瀚的作品。2017年3日,“西湖志:王公懿 / 严善錞作品展”在毗邻西湖的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王公懿展出的新作让人惊艳。
就算已经老去,又如何?时时新,才好玩。
就如1992年她在法国学石版画,“太难了,石版是份体力劳动,画的时候没有觉得是在画画,这个放肥皂,那个放沥青,版做好后要印,我这边的肩膀彻底劳损了,到现在都有问题。”但就是这份体力劳动让她开了窍,“越过了对艺术刻意的东西,因为没有觉得在做艺术,这个宝贵的状态有人遇到过,抓不住,我抓住了。”
化解之道,在乎本心。
王公懿当年因为母亲的一句话而学画,“我妈妈特别浪漫,特别美,特别爱艺术,爱看小说、看电影,那个时候还野餐,属于特天真的人。我小学时得了一点稿费,她让我交给班主任让大家用,这影响了我一辈子,我绝对是跟人分享的人。”原生家庭影响终身,不世俗的父母让她终身与身外之物保持着适合的关系。
2013年某个夜晚,中国美术学院副院长高世名第一次认真读王公懿的画,“那些作品如曲似醇,令观者熏然若醉。如曲者甘洌生辣,纵情肆意;似醇者隽永沉厚,其味绵延。”
艺术之程,无始无终。任何一个停下来的画面,都不过是绘画过程中的一个临时切片,如同永不止息的河流上的朵朵浪花。“二十年来,王公懿东寻西觅、上下求索。在此过程中,她的不羁之心渐渐从容,她的画面也日益澄澈,然而其胸中尚有块垒,笔底犹有波澜,她的格物“日记”,向我们示现出她艺术生涯中的独特领悟——了了分明处,念念不停留。”高世名语。
(上文有部分王公懿的言论源自《艺镜时空》王公懿专题纪录片,特此感谢)






▲2017年3月,“西湖志:王公懿、严善錞作品展”展览现场
Q&A
Q:雅昌艺术网
A:王公懿
Q:这次的《西湖志》是命题创作,此期间您的状态如何?
A:我刚开始做《秋瑾》就是一个命题创作,从那之后就开始随性创作,后来一大段时间我的作品都是日记,记录自己当下的状态。2016年,高老师给我这样一个任务,很有压力,其实是好事,避免泛滥之舟到处漂流。因为怕对不起这个展览,拼命地画很多,但实际上仍然是在生活节奏松散的状态下做的,不过这个松散不是说我在做别的事,而是说我的脑筋没有想别的事,也并不是说一天画8个小时,我认为这是非常傻的状态,要始终保持对自己作品的陌生感,这个特别重要。
其实每个人都有这个能力,可是当这个情境发生时,很多人没有捕捉到,我因为这种经验多了以后,好像找到了一种技术让这种时刻尽量多。要知道,工作越兴奋的时候越要停,觉得特别顺畅的时候往往是在重复自己,这个时候要把自己勒住停下,一般人舍不得,我很舍得。有的时候,画完这张画,自己在第一时间里并不知道好或不好,然后就把它搁在那儿,冷眼看,有时候看一个礼拜,有时候看一个月,有时候更久。某天会觉得,不错,有点儿东西,这个时候它是新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慢慢培养这方面的经验,应该珍视内心那种没有被洗脑的像孩子一样干净纯真的东西,它不是老会出现的。
我很想跟年轻艺术家沟通,每个人是不一样的,要慢慢熟悉自己,什么情形下这个状态会发生,而不是被人洗脑。

▲王公懿 点睛绢草

▲王公懿 点睛绢柳

▲王公懿 温莎蓝系列蓝山

▲王公懿 温莎蓝系列蓝山2

▲王公懿 斜影 木刻版画 69x90.5-4
Q:如何在所有人都说不好的时候自信、清醒地保持判断?
A:就是远离人群。没有画好的时候,最好别给人看,为什么?有时候一个并不是很厉害的人说你这个不好都会影响你,我是一个耳朵根很软的人,怎么办?避免别人说三道四,我的工作室一般不让人进去,并不是保密,而是不要别人来干扰我的判断。我很幸运,周围有很好的老师,大部分都比我年轻。
古人有一句说的特别对:师古人、师造化,真实的生活和了不起的大师作品中间就是你的工作范围。
Q:怎样在二者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并为己所用?
A:绘画艺术的范围很小,你拿起笔来,无论毛笔、铅笔或油画笔,实际上都是手的动作。我记得我13岁时刚刚学画,初中美术组的老师跟我说:手的动作很重要,那个时候哪听得懂,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这句话就进到头脑里。我50来岁才懂这句话,为什么手的动作重要?因为内在生命力从这里抒发。有的人这个问题没解决,可以描得很像或很准确,但是不对。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更多的注重观念、思想,我觉得这缺乏了一个最基本的立脚点,就是用手画。我在美国上过一次课,印证了这件事。十几年前,当地一所私立大学叫我去上一节中国书法课,怎么上?我把宣纸裁成小块,什么都没讲,就说你们每个人画一条横线,画完贴在名字下边退后看,大家本来热热闹闹的,一看都不说话了,为什么?他们都看见了自己,不是照镜子的这张脸,而是内在的能量。比如有个男生很高很胖,结果小线抖抖的,特别弱,但一个女的,30多岁,瘦瘦的,线条却很坚强,他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就是内心力量的外化。
你去博物馆,看到的不是题材或内容,而是精神。比如一个苹果,世世代代都在画,到塞尚那里就不一样了。梅兰竹菊也是很多人画,都是好画,可是是不一样的好画。无论画什么,其实都是在呈现自己,所以从事艺术必须陶冶内心,因为技术的东西是有限的。你看我70多岁,这辈子念的书很少,技术的问题很有限,但生活锤炼了我的内在,这块我有一定的丰富性,如果我没有被它腐蚀或淹没,我就更干净或更有免疫力。
Q:道理都知道,能不能用到自己身上是天知道。
A:所以人不能够太着急,可能某些人特别幸运或天赋特别高,霹雳啪啦早早成功,有的人可能一直吭哧憋肚的东撞一头,西撞一头,最后还是行,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独特的东西,不要去羡慕或追随别人。
不过说简单做起来难,需要自己一点点地跟自己较劲,艺术就是一种表达,没人能替代。小孩生下来饿了吃奶,谁教他怎么吃奶?我不高兴我哭,谁教你怎么哭是美,怎么哭是丑?这么说可能有点儿极端,但是我觉得道理是这样。

▲王公懿 《海螺日记》系列部分

▲《海螺日记》展览现场

▲王公懿 《原谅我这一生放纵不羁爱自由》



▲王公懿 《树日记》系列部分
Q:您的画作面貌特别多样,其中有些我个人非常感兴趣,比如书法的运用。
A:我最早学书法是在央美附中,蒋兆和的太太肖琼教我临《九成宫醴泉铭》,那个时候完全没有概念,后来在杭州念研究生,留校后我就很喜欢写字了,但那时候仍然不清楚写字的意义。后来到美国我才明白它,一个人,远离中国文化,那时做版画的条件没有了,就用毛笔、宣纸、墨临帖,而且开始教书法,迫使我把感兴趣的东西弄清楚。有次我临王羲之的《心经》,临了一个月临不好,当时就火大,一想,肖像我都能画得很好,怎么这几个字写不好呢?反复反省,最后明白是我心里的状态跟王羲之没法比,而不是笔划像不像。
书法到死也有余地可以学,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想学习中国艺术,书法是一个捷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不花哨的手段,很容易一下子进入最本真的地方。

▲王公懿 山水 70 x 50cm ED12 铜版画 2001年

▲王公懿 《磊磊矗矗 8/9》 云龙宣 墨 75x144cm 2008年

▲王公懿 《FRUITS》 铜版画 1998年

▲王公懿 《洞穴》局部 生宣 墨 2007年
Q:您最打动我的是您的生活轨迹本身就说明了另一种艺术道路的可行性。
A:因为老有朋友问我,你这样怎么活?他们很焦虑。其实我活得很好,做愿意做的事,也养活自己。因为愿意做就会持之以恒,而且会前进,如果不喜欢遇到挫折就会拐弯,所以不要害怕,现在社会给予年轻人的机会非常多,就做你喜欢的,一定会存活下来。
我好像内心深处很乐天又不是乐天,好事坏事都是天上掉馅饼,计划的事情好像都没有实现,实现的事情都是外界掉下来的,或者是别人推你一把,踹你一脚。比如,一开始是我妈妈让我画画,高中老师推荐我到央美附中,其实当时我画的特烂,工作后在出版社也干不好,跟领导又顶撞,领导让我去考研究生,我说我考不上,他说我给你走后门,就这样,真的不骗你。
Q:但我特别好奇或本能地反问,您最后为什么还会成功?
A:我根本就没有想成功。我想成功的时候没成功,比如1980年我第一次得奖,第二年又有全国美展,我就很想成功,做了《炎黄子孙》,觉得一定能得奖,但那个画现在搁那儿都不知道。有的人有这种能力,想成功真的会成功,我不行。刚到美国,给我钱的重要人物死了,没钱了,自己要挣钱,朋友说你画这个能卖,我认真地画了大概十几张想卖,可现在还在那儿堆着呢。美国有个画廊,7年之后来找我,怎么找到我的呢?我的一个学生是名心理医生,跟那个画廊老板是邻居,他把我的画册推荐给他,他就来了,说你怎么在这儿躲了7年,我说我没躲,我不会说英文啊。然后我就给他一大卷画,没托也没裱,他说我需要5年的时间把你推出去,一年后他就死了。
所以我跟你说什么成功,活着就是成功,快乐就是成功。

▲王公懿与《秋瑾组画》

▲王公懿 秋瑾组画之二《热血》 木刻版画

▲王公懿 秋瑾组画之四《起义》 木刻版画

▲王公懿 秋瑾组画之六《牺牲(二)》 木刻版画

▲王公懿 秋瑾组画之七 《秋风秋雨》 木刻版画
(部分作品图源自《艺镜时空》王公懿专题纪录片,特此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