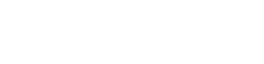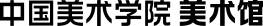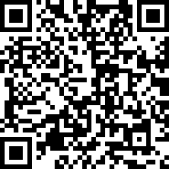老先生的相貌先就长得不一样。这张脸非常不买账,又非常无所谓,非常酷,又非常慈悲,看上去一脸的清苦、刚直、坦然,骨子里却透着风流与俏皮……可是他拍照片似乎不做什么表情,就那么对着镜头,意思是说:怎么样?我就是这样。

张漾兮 1957年
这是陈丹青在《笑谈大先生》里写的,写得传神。我一看,老爷子就是这样的啊。后来去四川美术馆看刚开的热展“刀锋民魂——张漾兮先生作品文献展”,看到三四张漾兮先生木刻印出来的鲁迅像,舒缓多了,慈悲劲不减,好像鲁迅要从画片里走下来一样。陈丹青说他喜欢看鲁迅的照片,他的样子,以为鲁迅先生长得真好看。要是仔细看过漾兮先生的木刻鲁迅,陈丹青恐怕得有新想法。

《鲁迅先生》 木刻 33x24cm 1948年

《鲁迅与瞿秋白》 套色木刻 38x51cm 1956年

1954年 张漾兮与张怀江、丁正献赴上海鲁迅纪念馆收集鲁迅题材的创作素材
“刀锋民魂——张漾兮先生作品文献展”要在四川美术馆展到4月11日,这展确实火了。开幕当天,我听了张漾兮先生长子张鼓峰的电视台采访,他下午还有个捐赠展在四川美术馆开,也画得好,一本厚厚的画册里,好多作品我都爱看,比如《春江月影》(软片版画),《黄山云松》(水印版画),一些水墨作品很有想法。张鼓峰感慨,自己本身也从事版画创作,感谢父亲身体力行,在艺术上和教育上给予了指导。他很感谢母亲多年来追随父亲张漾兮,在特殊年代将父亲每一幅创作都保留完好,才得以留存现今的全貌。他注意到主办单位打造的这场展览,毫不逊色于之前中国美术馆和浙江美术馆的展览,张漾兮的家人代表在开幕式上也这么说。工作人员很用心地将小小木刻放大到很多倍的喷绘招贴,哪怕随性一些的设计、切割,都好看,“震撼而用心”,让参与观看的观众们多角度看到在那个历史时代下,父亲创作的完整内容和清晰线索。策展人冯石布展期间给我发了些照片,用心极了,招贴幕布很有当代设计感,灯光打上去像时光再现。

记者采访张鼓峰

四川省美协副主席、版画艺委会主任武海成致词

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蔡枫致词

中国美协版画艺委会副主任、四川省美协主席阿鸽向张漾兮家属颁发捐赠证书

开幕式现场云集了许多版画名家
我之前对张先生实在不熟,后来报社大周末副刊的负责人蒋庆提醒我他写过张先生:《他刻下了成都人当年的苦日子》,读了两遍,算是了解了张漾兮很多在成都的事情。文中提到张先生两个女儿——在杭州的张芦宛和在成都的张黎前最近十年做了一件事情,整理和归纳当年父亲的作品剪报。这些剪报有很多都发表在1930年代、1940年代的成都报纸上,“一次又一次枯燥的搜寻整理,张漾兮刻刀和画笔下的老成都越发清晰而真实。”






展览现场
我于是觉得同样作为媒体人,张漾兮那个时代以刀笔为旗枪的斗争力,说白了,还是胆子大,而且大得很。展览开幕当天下午的学术研讨会上,我注意到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研究员蔡萌提到的几句话,有意思,今年中央美院要接连做李桦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展、王琦的百年诞辰展,纵览这版画体系展览来看,“要有作品很重要,作品留下来更重要。”张漾兮作品全貌被家人精心保留下来,十分难得,令人感动。从张国士到张漾兮,名字换了,但这透露出他个人那种意欲在变动不安的年代随波径流之“姿”,但骨子里他却有一种向下唤起的斗争性和力量。抛开那些时代因素和个人情怀,单从版画艺术本体语言来看,他的作品从语言、材料、状态来看,都很优秀。最喜欢他的那些水墨作品,和蒋兆和某个精华时期的作品难分伯仲,“小飞白特别迷人。”

《成都车码头》木刻 21x18cm 1945年

《我们自己的队伍来了》黑白木刻 24x33cm 1949年

《抢救2》木刻 41x56.5cm 1963年

《送饭到田间》木刻 26x68.5cm 1956年
我注意到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委会副主任、四川省美术家协会主席、神州版画博物馆馆长阿鸽特别诚意地感谢张先生家属将重要的部分作品捐赠给神州版画博物馆。“受鲁迅发起的‘暑期木刻讲习班’的影响,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四川作品抗战大后方逐渐成了新兴木刻运动的重要场域,中国近现代第一代版画家们在这里生活、创作、组织社会活动,以版画作为媒介,积极参与到中华民族抗日救亡的抗争当中。抗战期间围绕四川进行的版画活动,不仅充分体现了中国近现代版画所独立蕴含的创造性,更以其入世精神确立了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现代绘画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风格流向。张漾兮先生便是其中佼佼者——他不仅是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先驱,更是全程的参与者、见证者,还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第一代建设者。”

《祥林嫂》木刻 26x12cm 50年代

《开镰图》木刻 36x54cm 1962年

《新到的画报》水印木刻 47x35cm 1954年
“新中国文艺事业的第一代建设者”,这名词熟悉而又遥远,我看到在四川美术馆展厅里,文献展柜里展示的,几乎是新中国文艺事业的一芳倒影:《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斗争》(郭沫若)、《新的人民的文艺》(周扬)、《革命文艺运动总报告》、《国统区美术工作》、欧阳予倩、田汉、冯乃超、东北画报社、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反“翻把”斗争光荣灯、工人舞、爸爸参军独幕话剧……这些文稿像串联起来的年月符号,那股气隔着玻璃柜都弥漫得出来。
这些年龄比我还大的纸页,躺在那里,像是一群垂垂老矣的青年。






张漾兮先生文献陈列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刀锋民魂》一文中提到,张漾兮先生的一生可分为两部分,前半部分是1949年以前颠沛流离却又奋战不已的时期,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抗战斗士。后半部分是在杭州西湖之畔的美院度过的,那是一段肩负重任、与美院的成长相伴相行的岁月。我突然想起两件特别喜欢的西湖作品:1954年他的套色木刻《西湖风光》、1960年的套色木刻《西湖西泠桥》。我一度有冲动想把《西湖西泠桥》作为我新书《乌鸦穿过玫瑰园》的藏书票。可惜后来版权问题未能如愿。好遗憾。

《采茶女》水印木刻 21x26cm 1956年

《平湖秋月》水印木刻 33x42cm 1960年

《西湖西冷桥》套色木刻 37x42cm 1960年

《牧歌》套色木刻 45x31cm 1954年
四川美术学院教授、批评家王林在研讨会上说,张漾兮先生很明显地受到了四川汉画像砖的影响,那其中满幅构图的特点被张先生敏锐地捕捉到,同时他细致地看到了成都人、四川人生活家的精神,把那股浓浓的生活味道体现了出来。“创作中,那平民的兴致、生活化的诉求,对苦难的关注和同情,对底层人文的关注,永不过时。充满了现实和真实的意义。”在版画的民族化领域,我们要用有差异化的文化意识来看待现当代的艺术创作。这点我印象很深,我翻到浙江省版画家协会理事,张漾兮先生的学生俞启慧在《版途驼铃》里写到的一个细节,真是好看:张老师在给我们做下乡前的创作讲座时,强调要深入生活,他举例,他曾观察家乡的剃头匠给客人剃完头后挖耳朵的情景:顾客因耳朵被挖时,既紧张,又痒飕飕的,故表情显得错综复杂,往往一只眼开,一只眼闭,直到挖完了,才长长地舒出一口气“舒——服”。(当时他用四川话道出,大家受到感染,爆发出哄堂大笑)

1949年 张漾兮到北京参加第一届文代会和王朝闻合影

1957年 张漾兮和版画系教师与罗马尼亚版画家萨波.贝拉一起探讨版画艺术

1955年 张漾兮先生访问匈牙利、罗马尼亚期间留影

在罗马尼亚与与各国艺术家一起参观交流

1958年 张漾兮在绍兴作美院师生下乡总结报告
中国美术学院版画系主任蔡枫说得好,我一直记得,这场展览颇有亮点,中国版画民族化,每个时期都有一些差异化的研究,张先生很早就对版画教育思想定了调,1955年请青年教师进入荣宝斋学习传统水印木刻,是有前瞻性的,用一种本土的民族的语言来表达。他去到东欧受到了一些刺激,那边的艺术家说我们的艺术怎么和他们的差不多,这激发出他要讲艺术进行本土化的民族化改造。“刀锋、民魂,很明智的,上篇,刀锋,批判现实,投枪匕首,下篇,民魂,民族化的思考和践行。张先生对鲁迅符号式的情感,很值得思考。茅盾说过,文艺作品不仅是一面镜子——反映生活,而须是一把斧子——创造生活。”

1946年张漾兮夫妻与五个子女于成都家

1956年夏 夫人雷朝仪到杭,家中合影

1960年代 张漾兮在杭州

1962年 广东疗养
策展人冯石提到,在展览策划初期她一度纠结张先生成都人的身份,想着先生离家半个多世纪,这次要不要做一个回归展。但随着她对先生材料的掌握越来越丰富,人物理解越来越准确,她逐渐意识到张漾兮的家国情怀,或者说那一代人的家国情怀绝不仅限于“家乡”二字。在百年前全球化冲突最为焦灼的时候,那一整代人为了解决国人的身份焦虑和民族自信所投注的心血,其背后的格局是很大的。“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那一代人可以真枪实干的干革命,而转过头来又能如此精确地搞建设,他们似乎都不需要试验,也没有机会试验,他们的价值观形成于革命实践之中,又在后来的建设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这种价值观的准确性和随之而来的方法论的有效性着实令人惊叹。而更有趣的是,在建国初期的新中国,张漾兮绝不是孤例。正是遍布全国的这许多老先生们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一锤定音’,决定了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艺的大格局,也深刻地影响着当代文艺的未来方向。”



展览现场
实际上,在展览开幕前仅一个月,她才最终决定调整原有方案,借展先生同事、学生的作品,作为先生艺术思想的文脉补充。这样区别于前的策展思路很快得到了四川美术馆领导和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版画系的充分肯定与支持,这才使展览能够以张漾兮先生一生的艺术实践为个案,最终呈现出一个从革命年代走出的艺术家重建家国精神和寻求民族自信的完整线索,以及基于这条线索所生发出的更多探索方向。在展览现场,她特别为先生重要的作品添加了详细的展签说明,观众们可以在现场看到在建立中国第一个专业美术学院版画系的第一年,先生用中国传统材料与技法为学生们示范的第一幅水印版画,而在转过身的整个正对面,则展示着十五幅由先生的同事、学生创作的,在中国美术学院版画民族化文脉线索上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我想,我们总说典藏活化,到底该如何活化?先生的精神本来就是活的,它一直存在于后来人的创作面貌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