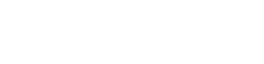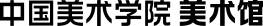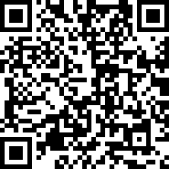在北京召开的第34届世界艺术史大会,有三个特色区别于以往各届。首先是得到了中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开幕式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庄严气派。其次是会议宗旨以一中一英表达:英文重申该国际常设学术活动的一贯宗旨,而中文强调中国艺术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重要性。最后一个显著变化是将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Art History改为World Congress of Art History。一字之改,赋予这个大会以真正的世界性。

曹意强,《贵阳风景写生》,毛笔餐巾纸,2016年8月23日
世界艺术史大会(以下简称CIHA)是艺术史成为大学学科的产物。1873年成立之时,艺术史在德语国家不仅已是大学教育科目,而且为拓展整个人文研究注入了新思想、新方法。其中一个重要的贡献就是催生了文化史。1860年,即CIHA诞生13年前,巴塞尔大学艺术史教授布克哈特出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率先提出了整合处理某个时代的史学方法:即把特定时代的绘画、雕刻、建筑等艺术与其日常生活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研究。布克哈特以视觉艺术证史,其成就使艺术史研究的重心牢固地确立在了文艺复兴领域。而主导西方艺术史研究的模式,如形式分析、图像学、精神分析、艺术社会学等,皆由此衍生不息,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
现坐落在伦敦大学的瓦尔堡研究院一直是文艺复兴研究重镇,更是传统出新的温床。该研究院旨在回答的核心问题是:古典传统对现代究竟具有什么意义?其追问从意大利文艺复兴图像为出发点,跨越所有的学科范畴,如今时髦的跨界方法,其实早已成为该院的研究常态。20世纪主要的哲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史家都与该院有密切的关系。其整合性的取向也体现了对中国艺术的关注。长期担任该院院长的贡布里希,早年求职时,其讲演的题目是《中国艺术对欧洲的影响》。他曾与好友库尔兹发奋学习中文。库氏博学多闻,其遗著探究非欧洲因素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堪称世界艺术研究的奠基之作,可迄今仍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当前西方艺术史出现两个趋势:“世界艺术硏究”和“视觉文化研究”。这两个思潮其实都跟瓦尔堡学派有深刻渊源,北京召开的CIHA也与之不无关系。传统艺术史关注经典作品,瓦尔堡在上世纪初参加第12届CIHA时就指出,传世图像是打开往昔心性的钥匙,艺术史必须跳出经典杰作的局限而重视次要作品,包括实用艺术。如果视觉文化研究旨在扩大图像范畴,那么世界艺术研究则拓宽探索的视野。北京大会特邀约翰•奥涅斯教授在开幕式上作主旨发言,具有象征意义。奥涅斯早年在瓦尔堡研究院攻读古典建筑与艺术史,导师是贡布里希爵士。奥涅斯于1991年在英国策划了“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国际研讨会,邀请贡布里希和苏里文进行对话。接着他创立了世界艺术学院,多次组织学术会议,系统地提出了“世界艺术”观念。《世界艺术》学刊在此基础上创刊。我参与了这项事业,回想起来,1997年,在潘天寿基金会支持下,我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策划举行的“20世纪与中国绘画”国际研讨会也是世界艺术研究的组成部分。当时应邀参加会议的几位重要学者,19年后重回钓鱼台出席世界艺术史大会,见证了中国艺术史的巨大变化。

曹意强,《贵阳风景写生》,毛笔餐巾纸,2016年8月23日
20年前的中国,艺术史还是美术学院的辅助学科,而今天,中央美术学院和北京大学联合主办了第34届艺术史大会。在2000年伦敦召开的第30届会议时,我负责主持第17分会,议题是“延迟与永恒”。这个主题的设置智慧源于中国古代画论中“艺无古今,迹有巧拙”的思想,同时表明艺无中西之分,唯有妍蚩好恶之别,艺术如此,研究亦如此。在大会开幕式上致辞时,我曾提到:中国艺术和画论可为世界艺术史发展提供灵感,而相反,针对我们自身,就应当考虑如何在国际艺术史的参照系中去发掘中国艺术和画论的独特价值。这应是我国举办CIHA的真正意义。
中华文明历史悠久,在很多方面曾经走在世界其他文明前列。中国现存最早的画论出于公元5世纪谢赫之手,而至9世纪,已形成完整的体系,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论述书画之起源,绘画的社会功能、智性体系、材料媒介,以及品评标准。在西方,第一部画论诞生于15世纪意大利,16世纪才出现第一部集艺术家生平和批评为一体的艺术史著作——瓦萨里的《名人传》。然而,中国领先于西方数世纪,这是往昔的骄傲,决非今天的成就!唯当将之转化为新的传统,这才属于我们今天的成就。学术乃天下之公器。一地一国的优秀传统,是人类共享的遗产,其继承出新不囿于产地,唯有耕耘更好的土壤,才能使之抽发新枝。
人类思想真谛在至高境界处是相通的,我们可以从柏拉图理念里窥见老庄思想,也可从老庄里读出海德格尔哲学。思想的谁早谁迟不是问题,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由此发展出有益于当代的洞见力,扩展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瓦萨里的《名人传》比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晚了7个世纪之久,这不能不说中国画论的先进,然而,我们对《历代名画记》的研究能与欧美研究《名人传》的学术成果相比吗?正是对《名人传》的批评研究奠定了文艺复兴美术史的基石,布克哈特的文化史,沃尔夫林的形式、风格分析,瓦尔堡和潘诺夫斯基的图像学,安托尔和豪塞尔的艺术社会学,贡布里希的艺术心理学研究,巴克森德尔的视觉习惯和文化研究,以及影响艺术史的其他方法如精神分析等,都建立在此基础之上,20世纪新艺术史也是对之反叛的结果。这在海外中国美术史研究中的印记颇深。

曹意强,《贵阳风景写生》,毛笔餐巾纸,2016年8月23日
巴克森德尔曾经指出,中国绘画批评术语能简明扼要地诉诸艺术效果,这是西方画论不可企及之处。我认为,中国画论有两个值得注意的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它从一开始就明确区分图像与文字的功能,以及各自的优长劣短。文不能表达者则以图绘之,反之亦然,明确界定了“画”表现、承载文所不能捕捉的自然、人文、历史意象。
在此,书画同源的观念,其含义远比后人理解的深刻。文字与图像是我们把握世界的两种互补、互进的手段。张彦远曾说画圣吴道子因“学书不成”才转习绘画。他称绘画“与六籍同功,四时并运”的断言即旨在强调:在探索世界的意义上,书画同功,而非单指书画用笔同体。从《说文解字》到《古画品录》,经由《历代名画记》直至《文史通义》,对书画智性功能的判别一脉相承。由此可说“书画异名而体同也”。绘画以其特殊的智性方式呈现三种功能:首先是道德教化,所谓“明劝诫,著升沉”(谢赫)、“成教化,助人伦”(张彦远);其次是探索世界奥秘,所谓“照远显幽”(裴孝源),“穷天地之不至,显日月之不照”(朱景玄),亦即“穷神变,测幽微”(张彦远);最后是我所称的“图像撰史”和“图像证史”的功效,前者所谓“立万象于胸怀,传千祀于毫翰”(姚最),或“前贤成建之迹,遂追而写之”(裴孝源);后者所谓“千载寂寥,披图可鉴”(谢赫),“指事绘形,可验时代”(张彦远)。
辞有陈鲜异同,思无古今中外。从英国艺术史家哈斯克尔教授的《图像与历史》可知,类似观念从古希腊萌芽,在18世纪进入哲学和史学思考,至19世纪开花、结果而成西方新史学革命,孕育出作为人文学科的艺术史。前者为因,后者为果。相比之下,中国画论的研究尚处于版本校勘、画论辑录的状态,由于隔裂上下文,讨论的重点集中在诸如“六法”的标点,或如“气韵”、“形”、“神”等术语的概念辨析上,一旦忽略决定其意义的上下文思想,就很难理解历代画论的品评之旨和品第系统。
正是在这个智性框架中,传统画论呈现出第二个值得深究的特色:它试图建立绘画的美学品质和类型价值等级品评模式,将个别画家的风格和类型与之对应评价。
以最早的“六法”论为例,它旨在勾勒出画之基本再现性质和方法,前者为“应物象形”,“随类赋彩”,“传移模写”,后者为“骨法用笔”和“经营位置”。“气韵生动”则是借助上述手段要达到的美学标准,指向艺术表现的生命力。“气韵生动”的含义在各时代发生了变化,但其内核一直未变,始终对应于品评等级的最高级别。在谢赫的六品中,录入上品者,不是具风神骨气,就是极尽生气妙趣而臻神境者。“气韵生动”等同于神韵笔力。而神韵气力不如前贤者则降列第二品。张彦远简化了谢氏的六品,并修改了朱景玄的“神、妙、能、逸”标级,提出自然、神、妙、精四个等级,在神品之上设置了更高的自然之品。自然即气韵生动。随着文人画的兴盛,逸品从唐时的别品而几乎成为“气韵”的代名词。
中国品评观念的演变史在世界艺术史中独一无二。它既评价艺术品质又作出技巧、类型和风格区分,并以此为尺度发展出一系列启发视觉关注的术语。18世纪欧洲艺术批评中曾出现按素描、色彩、构图等优劣打分,给画家定等级的尝试,但因缺乏包容性和视觉效果指向性而未流行。中国画论的品评系统虽然与文论、诗论(特别是《文赋》、《文心雕龙》、《诗品》)等有密切的关系,需要综合起来研究,但其自身所形成的体系特点是将艺术史、艺术批评、艺术理论糅为一体,其中还包含着丰富的创作论思想。正因为如此,很难按照如今的定义为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划界,它就是一部综合性论著。

曹意强,《贵阳风景写生》,毛笔餐巾纸,2016年8月23日
当今世界艺术史出现了专业细分、学术破碎化倾向,而且普遍忽略创作机制的研究。重新审视中国古代画论,发掘其活性基因,无疑有助于矫正当前艺术史学风。
从这点看,北京CIHA把主题定为“术语”有其深意。中国画论术语体系高度概括,而在当时相应的文化语境中运用,其意蕴不言而明,可这种特质在另外的语境中难以显明,而且有固化为套语的危险,如“气韵”、“写意”等术语已被不加区分地套用到中国绘画的本质上,成为陈腐的概念,失去了原初的生命力。
我认为,如果我们从历史的观念出发,在世界艺术史的大视野下,就应以西方研究瓦萨里的力度,深入而系统地探索中国古代画论,摒弃教条概念,重新发掘,重新激活其中隐含的活性基因,将之转化为新的创造,复兴中国艺术创作和学术的生命力。世界艺术和学术的历史证明了两点真理。其一,交流、迁移甚至冲突,是艺术和学术发展的动能。例如,这次北京会议有两个分会关注园林艺术。众所周知,中国园林从18世纪开始对西方造园艺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造园艺术引发了西方的思想革命,依照美国观念史之父洛夫乔伊的研究,中国园林艺术是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一个重要根源。由此将中国园林艺术纳入思想史研究,阐明了艺术对观念的塑造力量。其二,艺术和学术的国际化和民族性取决于其品质,而非地域,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和对之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即为明证。艺术和学术永远是天下公器,其作用之大小取决于品质之高低;只要是最好的,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中国艺术史的复兴有望于此。
(2016年10月19日于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