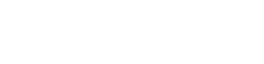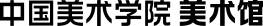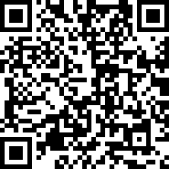安簃艺术家访谈 十六
何曦

何曦在创作中
摄影:徐明松
安簃:在“八韵:2021当代中国画邀请展”中,您的参展作品《越过山丘》和《直到永远系列》,画面物象都以骨骸的形象出现,骨骸意味着什么?
何曦:非生非死,向死而生。骨骸比生命更长,死亡才是永恒。
安簃:虽然您的作品中有使用工笔语言,但听说您并不喜欢别人把您归类为工笔画家?
何曦:对,我不喜欢把自己界定在某个绘画范畴里,特别是被称为工笔画家。我作画不打稿,也没有工笔画常见的草稿、拷贝和三矾九染的那些步骤,而是用写意笔法呈现一种有控制力的工整。我的表达是自由的,不把自己限定为某种语言形态的画家。同样,在题材上,我也不喜欢山水、花鸟和人物的分法,各个画种本没有严格的边界和技法限定。天开图画即江山,万物各有其美,无须门户林立。虽然我是从中国美院花鸟专业出来的,但从不把自己当成一个花鸟画家,只要是我想表达的,我都可以表现。

越过山丘
绢本水墨
90x180cm
2020
安簃:在您就读中国美院的时候,中国艺术界刚好掀起了“八五新潮”,杭州也涌现出众多活跃的艺术家,这对当时的您而言,有何影响?
何曦:我是1983年到1987年在中国美术学院学习的,这个四年刚好是“八五新潮”前后,可以说我们都是经历者,但我不是一个弄潮儿,这好像跟我的比较内省而自闭的性格有关。当时国门刚打开不久,大量的思潮涌进来,我们都如饥似渴地阅读,真的“天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其中尼采、叔本华对我的影响较大,还有卡夫卡,加缪等作家也是我非常喜欢的,所以我画里面那种荒诞的东西,应该是受了当时整体性的思潮的影响的。

直到永远系列1、2、3
绢本水墨
27×8cm x3
2021
安簃:纵观您的作品,发觉有两种不同的类型,一种是比较见意趣的,充满幽默意味的小尺幅作品;另一种是蕴含反讽修辞和充满人文关怀,又具有悲观属性的创作。后者有很强的连续性,构成了您创作的主线索。
何曦:对,我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平时我不爱说话,之前参加一个全国花鸟画主题的研讨会,主持人觉得我的作品跟其他人的都不一样,一定要我说几句。我说:“我不是拿花作为画的一个对象,只不过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一种心境。从小就生活在城市空间里面,我没有看到那种山花烂漫、莺歌燕舞的自然世界,我看到的鸟都是在笼子里的,花是在盆子里的,鱼是在鱼缸里的,我是画自己在城市中的样子”。这其实也是一种悲观主义的表达。我的摄影也是这样,拍别人注意不到的平常又荒诞的东西。
 地下室
地下室
纸本水墨
180×80cm
1995
安簃:常在朋友圈看到您分享的手机摄影作品,您的艺术嗅觉特别敏锐,总是能捕捉到那种荒诞而又引人共鸣的情景。作为艺术家,您是否还是更关心表达所指,而并不那么在意摄影语言?
何曦:对,摄影语言和绘画技法一样,并不是最重要,我看到的,我发现的才重要。其实只要长年累月的拍,总会形成自己的语言。我不故意去追求一种语言,我的日常思考和观察点肯定会造就特殊的语言方式,画画也是一样的。
 何曦摄影
何曦摄影
2021
安簃:看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作品,发现您在素描造型的基础上吸收了传统绘画中的点皴、线皴和积墨法等绘画语言,比如《地下室》、《灯下养鸟》系列。越往后,越能发现您在绘画语言上的开放性,面对传统语言素材库,您往往也是拿来即用。
何曦:在毕业后的那段时间,因为极力想表达,技法往往跟不上,显得稚嫩和单一。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技法语言也慢慢的成熟了。在90年代中期,我曾觉得中国画的语言缺乏那种强大的表现力,因此埋头画了两年的油画。尝试了之后,才发现任何画种都有它的局限,油画也有技术盲区,加上油画的那种粘稠感,让我觉得不爽,我还是喜欢毛笔画出来的那种很微妙的变化与淋漓尽致的表达。随后我就放弃油画,重新转向古代传统绘画。一路下来,从古人身上所学的那些东西,足够可以用来表达自己了。可能我还算是很敏感的一个人,平时也不太临摹,喜欢反反复复地看,看多了下笔也就会了,就像读诗百遍其义自现,有一天就豁然开朗了。

灯下养鸟之2
纸本水墨
150×80cm
1999
安簃:这让我联想到您创作的《标本》系列,其中就关涉到中国美术史上多位画家的作品。因为并没有全尽美术史上的画家,那么您是以一种什么样的逻辑去选择艺术家的?
何曦:主要还是中国美术史上公认的有代表性的艺术家,比如说五代至宋的“李范”、“董巨”、“马夏”,“元四家”,“明四家”,清代的“四王”、“四僧”等等。中国山水画史上有名的大家,我几乎都捋了一遍。其实也可以从笔墨和构图中,窥见我的好恶。
安簃:我看您这一系列作品,得到了两种不同的启示:一种是它告诉当代人,我们丰厚的传统经典,已经被陈列在博物馆里,成为了标本;另一种就是您的创作方式所宣示的,这何尝不是我们当代人活用传统的一种方式。
何曦:虽然我特别喜欢传统艺术,但是我不会跪到在前人的脚下。学习,就是要为我所用,要转化成你自己的表达方式。比如你学了文言文,你非要用它去和当代人作日常交流,既没必要,也行不通,但你可以把一种语感的精髓传达在字里行间。所以我学习了古代传统,就必须用最传统最深厚的笔墨作出最当下的表达。

标本·倪云林
纸本水墨
175×165cm
2013
安簃:从1999年调入上海画院,到2020年退休,您在画院工作了21年,您怎么看待工作单位对您的影响?
何曦:原以为进了画院可以一门心思搞创作了,其实跟我想的不太一样,上海中国画院也跟其他省份的画院不一样,我们专职画师会有很多的行政工作,除了创研室的行政工作外,我还兼画院画库的管理工作,画画大多是在工作之余。当然进了画院你的市场会好一些,但你自己得把持得住,如果一味迎合市场,你就完了。我进到画院之后有一段时间,市场也是特别好,而且收藏者会规定你画的内容,比如荷花、竹子之类,什么好卖画什么。没多久我开始醒悟,如果这样画下去,能见到的何曦就是这种被规定的面目,我那些苦心经营的作品就没人认可了,艺术不可能两条腿走路,“要么庸俗、要么孤独”。所以应酬的画,后来我都不再画了。另外,在画院里,也经常会有一些主旋律主题性创作,我曾画过一张“抗战”题材的作品《1937,我的家》,我没有很直白的去表现,而是通过乌鸦和被肢解的桌椅来象征战争所带来的破坏,我希望作品不要一目了然,不是事件的图解,不是浅白的歌颂和迎合。不少人说我不太像一个画院画家,这对我而言,可能是一种褒义,但我也深深感谢画院成就了这样的我。

1937,我的家
纸本水墨
145×290cm
2005
安簃:今年7月,您在宝龙美术馆举办了大型的个人作品展,展出了您近20余年的代表性作品,您自己是如何看待这次展览的,有回顾性的成分吗?
何曦:不能算回顾,只是一个阶段的呈现。因为我觉得还不够,也真的不知道以后会画成什么样子,我想只要自己还没有停下来,就不是回顾。
安簃:在接下来的创作中,您对自己充满了什么样的期待?还是说您正在实践新的项目?
何曦:在创作上,没有很大的目标,我是走一步看一步的。一直用围棋来形容自己的创作状态,下一步怎么走都是根据当下的情况所做出的斟酌。明年五月份在上海跟画院一位我尊敬的前辈有一场双个展,策展人希望我拿出新作品来,这正合我意。因为今年有了宝龙美术馆的个展,我不愿意再重复拿那些作品出来再展示一遍。时间不多,工作量会非常大,但我是一个工作狂,加之已经想好要画什么了,就觉得自己应该没问题,一张张呈现出来就是了。无论大画小画,我都不喜欢打稿子,这样也就节省了不少时间。我总觉得如果反复打好一张稿子之后,再画一张正稿,状态虽然稳定,成功率也高,但却缺乏激情,不太符合我个人的作画习惯。我喜欢处于一种磅礴而理性的状态中,在一种持续的情绪中去一鼓作气地创作。

直到永远
绢本水墨
180x90cm
2019
 摄影:李喆
摄影:李喆
何曦
1960年生于北京,1987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
上海中国画院画师、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上海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上海视觉艺术学院教授、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
个展
2021
直到永远——何曦作品展,宝龙美术馆,上海
2019
画说经典——何曦作品展,东京中日友好会馆,日本东京
2015
迷宫——何曦水墨作品展,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杭州
2013
在恰当与不恰当之间——何曦水墨画展,苏州博物馆,苏州
2006
何曦作品展,上海中国画院,上海
群展
2021
八韵——2021当代中国画邀请展,安簃艺术空间,上海
2014
第十二届全国美术大展,天津美术馆,天津
2010
首届中国画双年展,浙江美术馆,杭州
2009
第十一届全国美术大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2004
第十届全国美术大展,中国美术馆,北京
1994
第八届全国美术大展,上海美术馆,上海
出版
《何荷》
《何曦画集》
《南有嘉鱼》
《迷宫》
《在恰当与不恰当之间——何曦水墨》
《艳若桃花——何曦摄影》
获奖
2009 作品《陌生》获第十一届全国美展银奖
收藏
美国波士顿美术馆
中国美术馆
中华艺术宫
苏州博物馆
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
上海中国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