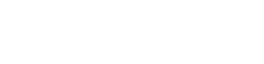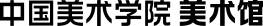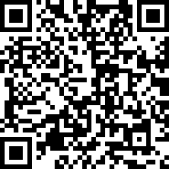当代艺术是否可以在纷繁的城市空间里寻找到另一种解?为了回答这一疑问,艺术频道开启全新子栏目——城市计划。通过实地探访隐藏在市井间的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私人画廊、文化社团等独立艺术体,城市计划希望走出艺术学院与大型机构的藩篱,调用一种在地性的书写方式,在微小的主体上发现一座城市的可能性。本期是城市计划的第一站——杭州,我们邀请了三名独立艺术空间创始人——恰好都是女性,讲述她们与一方“我可以说了算”的天地之间的碰撞。
paral:
paral: 一条街的内与外
观察者:徐梦艺
故事开始于1920年1月的美国,宪法第18号修正案——“禁酒法案”生效:凡是制造、售卖乃至于运输酒精含量超过0.5%以上的饮料皆属违法。为了不引人瞩目,转移到地下的酒吧营业者会要求客人“Speak Easy(小声点)”,因此地下酒吧也被叫做Speakeasy。它们大部分都开设在地下室、阁楼、后院等相对隐秘的地方,有着常客才知道的入口和口令,甚至被伪装成咖啡馆、沙龙、餐厅或者理发店等。

基于Speakeasy带来的灵感以及对酒吧文化的热爱,从事艺术工作的张梦渊逐渐形成了一个创建“Speakeasy+艺术空间”的构想。2021年,“paral:”于中山北路8号开业。“paral”即为平行,“:”是两只原点,寓意着艺术空间paral.space与酒吧 paral.bar一同出发。沿街的部分是展陈空间,与空间以一墙相隔的里间是酒吧,两个空间相互独立。在中山北路这样的传统商业街区,艺术展览的橱窗跳脱其中,带给来往观众新奇的视觉体验。因此开业以后没多久,“paral:”就成为了杭州的“新晋网红”。目前paral.space已经举办了两位艺术家的个展。

—
Q
怎么看待“paral:” 在社交媒体上收获的“流量”?
A
我并不介意大家认为“paral:”是一个网红打卡点。毕竟,曝光度高意味着内容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网红”属性的的确确帮助我们触达到了更广泛的人群。甚至就现阶段来说,“流量”是让人惊喜又意外的事情。我们没有预料到,“paral:”会在短时间内获得这样的关注。因为,建立“paral:”的初衷其实是为自己建立一个理想国,展览的艺术家与内容更多出于个人的喜好与判断。
作为艺术行业工作者,“话语权”一向是我关注的重点。在大机构大公司中,个体的声音、年轻的声音往往被不公平地埋没,我们没有改变状况的能力,但我们想要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划出一小片相对自由的空间。在这个地方,可以喝到喜欢的酒,邀请到喜爱的艺术家,让缺失展览空间和机会的艺术家和策展人们在这个空间里说了算。这可以说是一个任性的选择吧,但现代社会往往缺乏这样的任性,大家仿佛早已经习惯了置身于压力和妥协中。
所以我们的艺术家也好,观众也好,酒客也好,他们如果在别的地方感受到了压力,这种压力也许来自于生活、工作或者是艺术体制不完善带来的困难。我们希望他们都能来“paral:”,在这里,一切都挺简单的。

Q
在paral.space中办个展的艺术家,你是如何选择的呢?
A
目前办过展览的以及正在接触中的艺术家,都是我很喜欢的朋友,或是经朋友推荐的艺术家,之后我们也会慢慢开放公开征集的渠道。我很看重“聊得来”这件事。艺术家总有一些很妙的点,或者说,人格魅力,你是可以通过言语和交谈捕捉的。当和一个“聊得来”的艺术家合作时,是很令人享受的。


Q
作为归国留学生,对于国内的艺术市场你有什么看法?
A
我之前学习的是艺术管理,当时学校将这个项目分为了营利性和非营利性两个方向。前者针对的是未来想要在画廊、拍卖行、艺博会等公司、机构工作的学生;后者则是提供给对美术馆、公共艺术等领域更为感兴趣的学生。国内大众大多不清楚这两者的区别。具有公共教育意义的美术馆靠门票也不一定可以回收展览成本,但若门票价格偏高,便会有被指责“不值当”的可能;画廊无需门票,自由看展,但实际上是靠售卖画作给私人藏家而获得利润。
当然,造成公众对艺术行业认知混乱的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国内艺术行业制度混乱。我身边有许多在行业内工作的年轻朋友,虽然挺难的,但大家都股着一股劲,抱着对行业的热爱在工作。我本职工作的领导曾经说过一句话就很有意思,她说“别人说我们是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其实是在摸着自己过河”。希望我们这些石头们,和整个行业都会越来越好。
Q
你对“paral:” 有什么期待吗?
A
我回想了一下创立“paral:”的初衷,其实是一种抱有反叛意味的,简单直率的自娱自乐。我希望这个空间今后能够保持这份“倔犟”,作为一个年轻艺术家超脱于机构权威之外的表达场所、聚集之地,不断产出能够让路人忍不住侧目的有趣内容,观察门口的路人是我最喜爱的事。


啥空间
白盒子“便利店”里的艺术实验
观察者:谢闻
替代空间(alternative space)是一种发端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前卫性艺术实践,其所谓的“替代”是在既有主流艺术体制外给出另一种艺术的空间方案。早期替代空间具有特殊的历史语境,一个替代空间往往要能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发挥前卫艺术的批评作用。位于杭州武林路沿街的啥空间(Schein Space)就是一个融入社区的替代空间。在啥空间的微信公共号上我们找到了这样一段文字:“啥空间是由便利店转化而来的过渡型空间,我想因地制宜和艺术家合作,根据当时当地的情况把无限大的展览融入到24小时/7天可观看的沿街店铺中。”
啥空间在2021年5月22日举办了第一个展览《放学以后》。在此之前,这里原来是一家叫做“公式便利店”的便利店,四周是商铺和社区,来参观的人说“不太显眼,乍一看上去还以为是一家施工中的便利店”。现在的啥空间是一个结构简单的半白盒子空间,9月展览期间的墙面上还有之前展览遗留下的钉洞(艺术家坚持保留),进门后左手边墙角置放了驱蚊水、矿泉水等用品。


“公式便利店”是上一家店铺的店名,一直未换招牌
啥空间成为了沿街的一份子。为了贴玻璃静电膜不产生气泡,空间的创始人也是唯一的员工——宋瑶专门请旁边店的中国移动小哥帮忙。她说自己和街坊的关系都不错,移动展墙很重,有时也会叫旁边店的人来帮忙,而珠宝店可以用卫生间。附近的人会来观看展览,出于好奇心而来又产生了“看不懂”的不解,在“对当代艺术的距离感”与“日常联系”的张力下,社区与啥空间的联结似乎还有很多可探索的。
宋瑶回应关于“初衷”的问题:“因为疫情的到来,许多艺术家或者美术馆减少了展览,这或许对“大”空间造成了影响。而对于啥空间来说,体量小,灵活性高等劣势反而变成了优势,这或许也是时代的产物,顺势而为。对于个人而言,尝试过朝九晚五的工作后发现这不是我想要的职业或者人生方式,所以在三十而立之前做出这个决定,迎接新的选择。”
从开幕至今已经推出过4个展览,可宋瑶在艺术家和艺术项目的选择上仍然处于一种实验阶段。在艺术家的选择和合作上,一方面艺术家会投稿,另一方面也在不同的网络平台上积极地寻找艺术家并寻求合作。宋瑶说:“渠道不重要。‘沟通’是唯一的笨方法。”展览周期一般为一个月,也可以更短,她同时也在计划未来有不同形式的艺术项目和活动。
首个展览是一位准艺术专业的高三学生岑笑儒使用多种艺术媒介创作了《放学以后》,探讨了她置身事中的“校园问题”。展览展现出了艺术家对不同媒介使用的稚拙和熟练的反差,对声音的运用模拟了课文朗读这一校园中的日常感知,同时创作融入了对于古典文学的个人体悟。

“放学以后”展览作品:《救赎之山》(The salvation mountain), 2020年, 布面丙烯,100×130cm

“放学以后”展览作品:《狂人日记》(Madman's diary), 2020年, 影像 影音 装置
啥空间日常限制开放,需要扫二维码添加宋瑶的微信才能进入,这种机制形成了进入空间和在外观看的两类观众。宋瑶:“目前展览的初衷是希望通过站在人行道上可以随时观展,门口也有工具盒中放置导览纸方便观众了解具体信息。如果想要近距离看作品,也可以通过扫公众号的二维码,菜单栏中‘关于进门’来得知密码锁的密码。一方面保证一定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容易统计。有574人关注,但我相信也有对空间好奇的路人,仅是一个回头的动作,也是我的目的之一了。”

啥空间第二个展览“冉鑫安:在你右边的山峰”布展中
宋瑶:“现阶段,啥空间是一个过渡型的空间,是临时的、琐碎的、快速拥有的、不断流动发生的,也可以说啥也不是,啥也都有。关于对空间未来的发展,我想坚持就是我的计划。”
后窗
破局者的行动网络
观察者:谢本颢
萧山的金城路上,宽敞大街的两侧还没被店铺填满。正觉得有些冷清时,一家装修奢华的会所猛然跃入视野,绕到它的背面,一个叫“国际商务中心”的写字楼才逐渐显现了出来,后窗——这个显得和外面的一切都有些格格不入的画廊——就藏在这里面。

后窗是个线上线下齐头并进的独立艺术空间,作品主要是中西方当代艺术。创始人希望后窗能作为一个窗口,让不被看见的年轻艺术家被人看见。和不少杭州新兴画廊一样,后窗也想填补杭州当代艺术的空缺。
后窗的线上画廊要比线下更早一些开始运营。主创团队希望利用这一新兴的销售模式打破原先的艺术消费理念,以及各阶层之间对艺术的不同理解。主创们挪用博伊斯和拉图尔的理念,认为人人都是“艺术公民”,而后窗是个“艺术行动者网络”。而线下空间是今年五月底才刚开放的。一进门,玄关的木质结构和暗暗的暖色灯光,它的现代感与许多冷冰冰或者花里胡哨的画廊都不太一样。玄关尽头再打开一扇刷着黑漆的铁门,才发现,这里面比想象的大得多。
简洁的空间里,一个像模像样的当代艺术画廊该有的,后窗好像都有:形状不太规则的展览区域,地上摆了许多下个展览的艺术作品;放了几张沙发的休息区,墙上有写着“Star Start”标语的霓虹灯牌;洗手间、会议室;甚至整面墙装满酒的吧台,这里都有。

我坐在休息区的沙发上吃着早上没来得及吃的三明治,等待主理人黄乖儿出现。结果来的是一位打扮有些酷、看上去十分干练的人,说话声音低沉磁性,与她的名字形成反差。
从吧台拿了两瓶啤酒,我们转移到会议室去,采访就开始了:

—
Q
创立后窗的契机是?
A
我一开始是在国外,因为疫情回来了。回国之前就有考虑过回到杭州能够做些什么事情。我问了很多朋友,发现搞艺术的朋友基本都去了上海,他们给我的一致反应就是,杭州当代艺术这一块还是比较欠缺的。我觉得如果不去上海的话,就在杭州做点什么,毕竟是自己家嘛。我本身是纯艺术硕士毕业的,之前在纽约也策过一些展,对策展也挺感兴趣,所以创立了后窗。

Q
后窗签约艺术家或者征集作品时有没有什么特定的倾向?
A
我们的方向就是青年艺术家,可能不是特别有名,但是品质一定要好,风格、媒介都不限制。作为画廊,我们也不会要求艺术家做什么样的作品,还是希望他们能有创作自由。不过也不能说全部都是青年艺术家,比如我们的下一个展览是星星画会,他们是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开端吧,我觉得也是重要的。
Q
如何理解后窗所说的“艺术行动者网络”?
A
“行动者网络”是一个大家都在讲的概念,在这里并不是指准确的原意。我们所说的“艺术行动者网络”,是利用线上与线下的共同作用,挑战现有传统画廊与美术馆模式,链接艺术公民与艺术创造者的一种模式。我们真正的意图就是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参与到艺术这件事情当中。
Q
对后窗来说,线上和线下画廊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A
线上和线下都挺重要的,甚至是相辅相成吧。有些人先知道线上空间,然后才来线下看。我们做线上平台就是想要拉近艺术品跟普罗大众的距离。很多人就算对艺术品感兴趣,也不知道哪里能购买。画廊的气场一般人又会觉得很难接近,会有距离感,而且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购买流程是怎么样。所以我们觉得把画廊放到线上对大家都很透明。

后窗的微信小程序
Q
你对艺术电商平台有什么看法?
A
目前来说,我对整个大环境是不太看好的,因为可能大家不会轻易信任艺术电商,收藏者们还是喜欢亲自或者找艺术顾问去看作品。但未来几年会有发展趋势,因为在疫情发生之后,国外的线上交易量是上涨的。
其实做艺术电商平台的第一步还是在做艺术教育,要先把群体培养起来。我们的线上平台也是作为一个空间,让大家能够看到这些艺术家的作品。
Q
在艺术与公共教育方面有什么具体打算呢?
A
我在考虑做一些讲座和活动,也可以找一些老师来上课或者合作。我在留学的时候发现西方大学教育在学科上是非常融合的,而且民众对于社会问题的关注度也非常高。美国博物馆的保安都能跟你聊艺术,也不说有多专业,但他们都是有这方面意识的。
Q
对后续发展有什么规划吗?
A
最近的一个规划就是要参加一下艺博会,艺术圈内还是需要走一走,不然接触面太小了。还有就是怎么推广出去吧。现在我们线上主要是做微信上的小程序,还是有一点限制,圈外的人不一定看得到,所以在考虑往其他平台上发展。
—
无论是从小生长在杭州的宋瑶,还是离乡多年后回到杭州的黄乖儿,又或者是刚在杭州开启一段新事业的张梦渊,三个年轻的艺术空间运营者都把杭州本土的“艺术生态”纳入了自己持续关注和思考的对象,但这份思考同时又催生出了三种截然不同的面貌。“paral:”将酒吧文化与艺术空间融合,鼓励新鲜有趣、充满年轻活力的艺术表达;顶着便利店招牌的“啥空间”进入城市中心的居民社区,坚持前卫的表达与批判;“后窗”想要打破艺术消费的阶级分化,继而意识到公共艺术教育也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工作。在交流、合作、打破和重组中,是人们朝向艺术本体的驱动力使得空间能够焕发出新的活力。
然而从长远考虑,独立艺术空间的可持续型发展仍然受限于具体的市场环境。是否需要采取一种长期稳定的盈利策略,是三个运营者都无法逃避的难题。在天平的两端,始终需要调节的是创作的独立与自律,以及市场与公众的期待。在观察者们看来,“返回当下”或许是一条可能的道路:通过与城市社区和居民社群建立在地的联结,形成依托于友邻的共同生活与生产的方式,一种全新的审美形式或许能从具体和细微的文化体验中出发。

策 划|杭 间 余旭鸿
公教策划|夏商周
执行统筹|薛佳音
本期主理|陈天琪
采访图文|谢 闻 谢本颢 徐梦艺
视觉设计|谢本颢
主 办|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公共教育与发展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