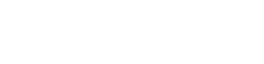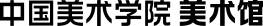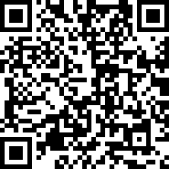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从一开始‘场’就不仅仅指向‘场地’,而强调‘现场、在场’。我们更希望在平地上翻出新土,这里恰恰是为那些不可教的留下空地。”
——铜场发起人金亚楠
铜场计划 Tproject 是由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支持的青年艺术计划,该计划策划团队由青年教师和在校学生组成,并自主进行项目的策划、推广和运行。在上一期的分享中,铜场通过疫情后的三个艺术计划展现了对集体创作的理解(详情请见:🔗艺术频道|铜场和它的三个计划)。时隔两周,艺术频道再次向铜场中的青年艺术家发出倡议,请他们聊一下自己具有代表性的一件作品,由此来展开对“个体”在“集体”中创作的思考与讨论。

“寻找某种落地感”
崔黎:图像中的我在佛罗伦萨Duomo广场卖“商品画”。我想了很久,如果我把这个事件称为艺术作品是否合适。如果我们从美术史里找定义,我的作品是个什么形式?借此机会我想聊聊(空间)边界延伸,一件待完成和待定义的(艺术)事件。

我在Duomo广场合法租赁了一平方米的摊位,和当地的画家们并列展卖了商品画。作为旅游景点的商品画,有着纪念品的功能,题材也都是当地的风景和古迹。与当地画家手绘有所不同,我展出的是一些仿画印刷品:我在网络上随机下载了当地古迹的图片,并用免费图像风格化的app以不同画风处理后导出,再分别打印在水彩纸、油画布、素描纸上,裱好展示。并把以上过程录屏通过手机app扫描图像时呈现出来。

该事件的的呈现有以下几个现场:
1. 展卖期间Duomo广场的现场
2. 手机app扫描图像时的虚拟现场
3. 记录该事件的图像与文字的现场
我在做完这件事后,不得不自我推倒该事件的边界问题,例如艺术形式的边界。
2017年在铜场,事件成为了大家集体“作业”的一个主要过程。随着“结果”变得次要,艺术形式似乎瓦解了。在这个经验之后,我个人再也无法“完成”一件作品了,在我的创作思路中,形式的边界被消除,艺术本身也似乎淡出了。这种状态竟然持续了3年的时间,直到近期我才开始渐渐找到某种“落地”感,在铜场年鉴画册里翻到自己写过的话,其中“人是空间的延续”也许就是我这几年的状态。

“对情绪的反复感知”

“筋疲力尽的制服”
阮媛媛:这是一件创作于2020年的作品,名为《筋疲力尽的制服》。将一套蓝领工作制服解构到缝制前的状态,由立体回归到平面。再选择用手将一块铅皮沿着布料边缘精确撕扯,得到同等的一份平面,撕扯下的剩余物被凝聚成了具有重量的石头的形状。所有情绪被化解在最后无法呈现的动作里,筋疲力尽地达成意愿。

试衣间计划“横向的铺展和纵向的延伸同样重要”
我一直将衣服作为介入身体与社会之间的中介去看待,衣服形象化的展现了身体与社会在某种程度上的对抗或者说是权衡的结果。这几年来在铜场我拥有了有限的创作空间去思考我所在意的问题,也在一步步的实践中摸索着零碎的线索,寻找整合的契机。
“将理论作为开始”
苏醒:这是上学期为了铜场三个计划的展览做的作品,我想这应该算是我对城市骨架计划的一个概述。

“侯潮门——星空想象与城市观测”
在做这个作品的期间,我翻遍了档案库里的各类历史老地图,然后将它们撕裂、并置,慢慢就会看到杭州这座城市是如何沿着钱塘江或西湖一步步生长出来的。我就是这样通过对于城市历史地图的研究,仿佛进入到了这座城市一步步扩张的路径之中(例如持续多年的地铁修建)。

“侯潮门——星空想象与城市观测”
但城市的扩张并不是我想讨论的重点,我想讨论的其实是历史与时间的问题。在这个作品里,历史仿佛不再是线性发展的了,而是被并置在了同一刻。这就像古代的人们在观测星空,把星星连接成了星座。但其实那些星星在观测记录的时候可能有些已经泯灭,有些才刚慢慢开始变亮,只是在观测的那一个时刻,他们都处在同一投影平面上,从而构成了那个星座的架构。在线性时间上,星星们不是同时存在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就不一定了。这也是我从理论学习转入创作实践以后的第一件作品。
“感受真切的存在”
蓝欣悦:有时我在做作品时感受到的不是自由,而是想法的枯竭。我在尝试理清自己的大脑之后,认为如果想要摆脱这种“枯竭”,就需要去进行一些实践“工作”。这种实践或许不是意味着去“做作品”,而是要去了解生活,用自我去体验真实和世界——阅读也是其中一种体验方式。做作品应该是一种厚积薄发,而不是像我现在这样有多少给多少——这也是我感受“枯竭”的来由。很多巧妙的作品虽然只展现了一面,但是它高明的地方在于,在这个“整体的一面”周围仍然有很多入口,让人可以看到背后那些“厚”的东西。我目前自身的拥有之物,就不足以成为“背后之物”。而在关于“信计划”的实践里,就让我感受到了很多“真切的存在”,这也是我想继续的原因。信计划对我个人而言也并不像一个作品,而是一个做法,一个行动。
“不断跟随问题”
彭胤瑞:“时间”总让我感到疑惑,它朝着“未来”这样一个确定的方向前进,而未来却又总是让人难以捉摸,充满不确定性。我们常常会有找不到目标、想要放空自己的时候,接着慢慢地被时间吞没,且对此感到无能为力。我希望通过对时间的重新认识,表达自身的限制感。
《偏移》展示的是我面向“未来”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原地沉默,一种则是不停奔跑。两种方式都在期待着转机,期待着“偏移”的到来。“偏移”始终没来,而目标的丧失也使得“我”进入了一种无时间的状态。作品中没有设置结果,因为我自己也还没找到答案。

“偏移”
“往前蠕动一点点”
朱丽瑾:《点不着点着点》试图通过几个“点”之间的关系,在展览现场制造一阵不可触的风、一个不断将周遭卷入的气旋。作品的三个组成部分对应三个变化的“点”,而作品中唯一确定的“点”在每个观众自己这里——多米诺骨牌的影像斜打在墙面上,对于每个观者来说只有在唯一的一个位置点观看时,画面才正对着观者自己。于是,原本立体的三组场景最终都被压缩回观者正对影像时眼睛框选出的画面的透视焦点。一切都坍塌回这个焦点透视中唯一确定的点。由此,观者由自身位置投射出的观看平面,成为了四方形的空间中立起的第五道平面,而观者自身的观看点在周遭变动不居的“点”之中则成为了那个唯一平静的风眼。
这是“感性沙丘”展览之后,对于“风”的再度展开。其实在“感性沙丘”中,多米诺的影像就拍出来了,当时还有一段关于电子蜡烛的影像和一段风扇吹布的影像。后来策展人斐然姐提醒我三件作品的展陈方式能否有些关联,甚至可以做成一件,我觉得有道理,但一直没有想好怎么做,只能搁置。再之后,在铜场做的另一个展览里反复调试,受到各种实地因素带来的推力刺激,直到展览开幕前的那天早上才串联起《点不着点着点》的整个想法。
在想法落地之前我会有很多顾虑,但是反复思量之后我一定得试试,然后回看做出来的东西,然后再次尝试。迭代过程就像是蠕动一样,用研磨身体的方式往前一点点。而铜场恰恰提供了研磨用的基石――在铜场的工作中遇到的人、发现的视角、铜场空间本身……
“迂回地接近不可能性”
赵如鹏:《一种局面》这件作品整体呈现时钟的样式,最下方的装置为黄铜制,呈断裂状态的混沌摆模型;中部为详细标注了各种参数的地图板,而地图下方由横竖各7列黄铜齿轮组成,它们都连接在背后的铁框上。

“一种局面”
上部为参考幻方(一种数学游戏,方格里的数字无论如何排列,通过某种运算方式总会得到相同的数字,丢勒在版画《忧郁一号》中使用该符号以象征一种“坏的无限”)和世界末日时钟(由芝加哥大学设计,其指针的位置会随人类社会爆发核战的可能性的增减而调整)的造型制作的钟面,指针接近零点却不再移动。整体来说,这是一个以时钟的面目出现的“世界机器”,世界停止了,但是没有人能保证一旦它恢复“运行”,事情是否会变得更糟。

“一种局面”
我对于不可能性有一种强制性的关注,在我的想象中,不可能性是各式各样的对于这个世界本身的冲动的本性,改革、逃避,甚至希望它毁灭,种种这样的冲动最后大抵是无法实现的。我将其理解为最为纯粹的悲剧的形式,这是一个危险的想法,但是通过为它建立模型去迂回的接近它,作为个体的我得以收获某种享乐和自我认同。

“一种局面”
“把作品做完的意识”

“Expose”
吕彦瑶:提到这件很少被提到的作品是:2019年是开始有“把作品做完的意识”后的一年,或者说是开始真正创作的年份。这与我的生活状态的变化有关,这种变化促使我开始意识到我和“其他”的关系,从而开始对客观事物进行探讨,这种探讨强调的是“探讨”这个过程,同时也指的是“探讨”这个动作。

“Expose” 吕彦瑶
参与进《Expose》这件作品的观众,会在我的身上通过Mp3听到右边地图上一些地方的声音,也会通过Mp4看到右边地图上一些地方的影像。这些设备装在这件衣服的口袋里,他们会好奇这些设备而伸手来取。网格布拉帘、地图、衣架和衣服,随着生活状态的变化,目前已经丢失,这些声音和影像保存在我的电脑里,部分播放器存放在地图上的一个地方。

“Expose”
“一件失败的作品”
武希文:这里我想可以谈谈集体创作这件事,我们第一次尝试用这种方式是2016年的“72小时内持续发生的事件”。当时的约定是从第一天晚上八点开始,整整持续三天三夜。参与这个计划的人必须共同行动,期间都不许回家,不许从这个状态游离出去。每个人都会有想要实施的计划,其他人就去协助他实现。当时参与的人除我之外还有:王闽南、王杨、易超、陈奇、章献、李新坡、蔡冠杰、崔黎、马新宇和童佳慧。一开始所有人都挺兴奋的,我们在龙新村拆迁的废墟里玩了几乎一个通宵,72小时其实很快就过去了,到第四天下午的时候大家都比较疲惫,所以一结束就各自散了。之后,这件事突然不了了之,我们大家好像都不太愿意提起。在一年之后的二工年展上,策展组提出要把“72小时”当作一个版块呈现,我当时写了两段话,叫“一件失败的作品”。应该很多人不同意我这样描述这个项目,但到今天我还是觉得这样描述是合适的,一方面,这个计划其实只有失败了才是完整的;另一方面,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这个项目是必然会失败的,但我们需要这个失败来为之后我们这个群体或是个人行动打开一个局面。

“72小时内持续发生的事件” 王闽南方案 《迹》
时间:21日夜晚 ;地点:转塘龙心村拆迁废墟;人物:72小时小组成员
我在刚拆迁的住宅区内发现了墙壁被拉扯过的痕迹,暗铺的线路电线已经被去除,因为拆迁不久,很多家具和墙壁都很完整,和墙壁的痕迹有着很大的反差,我决定利用这些痕迹,把小灯泡插在凹痕里面,把凹痕填满,再利用无线电原理,像抚慰伤口一样,依次点亮小灯泡,发出的微弱黄光,渗透进痕迹里。
“在废墟的墙壁上,留下的线路痕迹,笔直而又沧桑,我试图用灯泡去点亮每一个角落,触摸这干脆利落的伤口,废墟中的故事,总是给我们带来不清楚的‘痛’。”

”72小时内持续发生的事件“ 易超方案《一回等千年》
时间:23日下午;地点:象山路;人物:易超;协助:武希文 王杨 王闽南
笔墨、等雨、雨来、写字。
写一封信,通过雨水的传递。
曹志昊:2019年年底,雕塑系第二工作室同学在铜场集体创作了一件作品《纪念碑为谁而建》,同时也抛出了标题本意的问题,纪念碑为谁而建?历史上关于纪念碑的讨论已经在对其功能性和形式的叙述里,逐渐从描述转变为质疑,以往被盖棺定论的词义也被一次次地拆散和消解,对纪念碑固有形式的印象已经不复存在,同时也摆脱了类型学和物质层面的约束,取而代之的则是“纪念碑性”(monumentality)成为了“纪念碑”(monument)的主体,如阿洛伊斯·李格尔的描述,“纪念意义,或者说‘可纪念性’,不仅存在于有意立起的纪念碑当中,也存在于任何带有纪念性质的物体身上。属性从物质中被分离出来独立看待。”

“纪念碑为谁而建”
纪念性作为纪念碑形式之上的存在意义不可动摇,纪念性的受众则是面向一个特定的人群,给予他们群体的归属感和身份的认同。在我理解的这件集体创作《纪念碑为谁而建》里,作品的结构和命名也朦胧地指向了这个问题,为“谁”,而不是为“什么”,前者的语义针对能在这个纪念碑中找到群体归属感的人群,而后者则是纪念碑的纪念意义。特定的人群具体是谁?必须是人群吗?与权力、气氛、事件、空间和永久的观念有关吗?这个问题找不到一个准确的答案,答案或许是一个群体的质疑,也或许是一群人对纪念碑词义的再一次消解。答案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由此引出的疑问。
这座纪念碑的纪念性意义在它的描述里足够暧昧,甚至单独拎出了纪念碑的形式作为叙述。这是很冒险的举动,在纪念碑研究的层面上,“不为什么而做”的初衷本身就消解了纪念碑自身存在的价值,足以摧毁整个作品内部叙述的完整性,但是,这件纪念碑属于一个短期展览,它在展厅内搭建,它最终一定要被拆毁,事实上在它必须被拆毁,只有如此它才可以趋于完善。
从一群人搭建,展览,最后一群人拆毁这一系列的行为已经构成了“事件”的发生,“事件”不是指日常生活中发生的、作为明确事实的事情,事件向着更开放的“不确定性”和“可能性”,有着独特性的属性,撕开普遍性的包装,去洞察其中被遮掩的混沌,裂痕和边缘,感受共同存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绵延。或许纪念碑为什么而建,不重要,纪念碑为谁而建,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留下了独一无二的事件,一个完整的叙述。一个乍看奇怪但又逐渐适应的形式,一个特殊又完整的“事件”,足以成为群体记忆里恰如其分的纪念碑。

“xx年xx月xx日的纪念碑”
几乎是和二工展览的同一时间,我也跟进了一个关于纪念碑的方案,但是由于国外疫情太严重也没有办法落地,所以目前只能以方案的形式呈现出来。这件作品简单来讲,是一个可以在内部还原过去任意一天的气温和干湿度变化的玻璃盒子,甚至可以根据天气预报来模拟未来一天的变化。取名就叫《xx年xx月xx日的纪念碑》。纪念碑未必一定有大小和物质为尺度的定性标准,气氛,温度,气味,触感组成的记忆共同体可能同样可以承载“纪念碑性”的意义,记忆也会被这些突然间闯入嗅觉和触觉的因素唤醒。之前我有想过做一个人可以进去体验温度差异的玻璃房子,但是随后就否决了这一想法。纪念碑和观众之间一定是有距离感的,这种距离感可能是体量的大小,严肃气氛的阻挡,历史时间的隔阂,就像面对这个纪念碑时,可以知道它里面时刻在发生着温度的变化,但没有任何办法亲身体会它,就像记忆一样,可以无限接近却永远无法触碰。

“xx年xx月xx日的纪念碑”
//
每个青年艺术家都有各自所要面对的,关于艺术的“内与外”的问题。“我们的行为已经构成艺术性了,还需要做出一个艺术品作为最终的输出吗?”“是不是所有特殊事件都能算是艺术?”……诸如此类。但是艺术本身无法给答案,只能在集体或个人的具体应对方式中去触碰这些问题的脉搏。
创作最终还是从集体回归到个人,再从个人观照群体。而铜场一直在以集体的“事件”作为激发个体创作的切入口和培养皿。这些“事件”所触发的多重偶然性与思想交互时个体所生发的不言自明的那个部分,或许就是金亚楠所说的“为不可教所留下的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