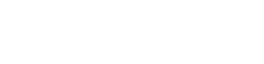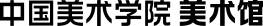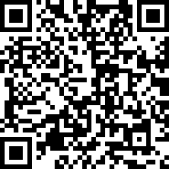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凡人抵御庸常时,天才已拍完短⽚。”
谈及自己担任评审的“2020NOWNESS中国天才计划”,电影制片人王子剑抛出这样一句话。自去年起,NOWNESS现在平台向新⽣代影⼈发出名为“天才计划”的短⽚创作邀请。从名字便可一窥其挖掘创意新锐的野⼼。12月12日⾄15日,历经三个月收件、从近五百部参赛作品中遴选而出的12部作品首先在线上及上海线下向公众开放。
12月17-21日,NOWNESS现在“2020天才计划”特别展映也将登陆杭州,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进5天展映。除了入围“中国天才计划”的12部影片,这一盛大展映还纳入了NOWNESS Global十周年经典展映以及三位中国艺术家柳迪、陆扬、陈轴的影像作品。
过去,短⽚常常被视为电影⻓⽚前必经的练习,在有限篇幅内创意的完成度很能检验出导演们对于拍摄现场和影像叙事的掌控⼒。翻阅阿巴斯的《⾯包与⼩巷》、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电⻋》、诺兰的《蚁蛉》乃⾄近处贾樟柯的《⼩⼭回家》,可⻅天才影⼈们早在他们练⼿的短⽚中便显露出日后极具辨识度的个⼈⻛格。
而从前⼏年重映的园子温、⽯井岳⻰、绪⽅明等在电影社团时期创作或在独⽴电影节中亮相的8mm短⽚,⼜或以魏德胜领头的台湾纯16影展的短⽚集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告别制⽚⼚时代,年轻世辈的独⽴影⼈,正是这样从“⿎捣”着简单的影像⼯具,碎碎念⽤短⽚记录着私密的自我心绪,开启了个体与影像的联结。
在选⽚和展映的同时,此次“中国天才计划”也有围绕短⽚话题对⼊围者进⾏采访记录。他们当中,有些具有顶尖的电影专业背景与重量级的国际竞赛履历,年纪轻轻就交出稳扎稳打、有发展成⻓⽚甚⾄类型⽚的潜⼒作品。
更多的创作者,身居世界各地,有多重专业背景,已不局限在“拍”⽚子的“导演”的身份中,有些甚而自⽐“虚拟隐⼠”,驾轻就熟地拼贴不同介质的影像、横跨多种媒介,即使是有完备的专业团队,也刻意选择量⼩好调头的短⽚,想要在多媒体艺术而⾮仅仅是电影的领域去思考和探索短⽚的语法。

而NOWNESS也是如此敞开怀抱,从一开始就不设限,剧情、纪录、时尚、动画、概念艺术和实验短⽚同台竞技。相⽐树⽴某种嫡系的选⽚⼝味,来自电影、⾳乐、媒体出版等各领域的评审则共同表达出对创意和想象⼒的期待。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在连续观赏过这些短⽚后,作为观众的我,整体新鲜与惊诧的感觉远多过当机⽴断的偏好与评价。常规的电影评价体系显然并不通盘适⽤于这些影⽚。
若说这些影⽚有什么共通趋势,一个最直观的感受是,成⻓于计算机和移动互联⽹⾼速发展的时代,这些日常在各种屏幕界⾯接触视觉图像的一辈,深受新媒介的影响。与印象中过去短⽚的粗糙质感不同,新⽣代驾轻就熟地使⽤各种软件与技术,甚⾄3D、CG的制作⽅式和帧率、画质影响下感官体验都被有意识地纳⼊考量。

《卫塞节》这部短⽚甚⾄直接采取了实时游戏引擎的⽅式完成,制造了一场惊⼈的视觉奇观,巨⼤的佛像以电子游戏的时尚质感显现,某个房间⻆落的⼩荧屏中播放着刚出现过的外⾯的⼤⼤世界;囿于⼀⽅天地的⼈接受着电子设备中“是否放⽣⻥”的拷问,此时窗外游荡过的巨⼤的⻥怪让⼈分不清究竟谁在笼中。
这些界⾯与时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来不及多去思考,声⾳素材将观众引向另一个维度,既有质感如素材般粗糙类似新闻采访的录⾳回响,也有疑似创作者置于⽚前⽚尾对于作品的阐释和自⽩。正如自⽩者所愿所⾔,声⾳和视觉元素营造的体验不同于⽂字的“解读”,这种感官探索亦可视作一种修⾏。充满灵性的宗教与形而下的技术竟以这样的⽅式结合同一,但细细回想,如今的CG渲染等技术的本质⼜何尝不是从“⽆形”中⽣发“有形”。

《卫塞节》
动画短⽚《⽩⾊的⻢》的创作者徐⾬洁同样在受访中表示出对于声⾳和图像动态结合的关注,一直有在尝试运⽤不同材质和媒介来做情感视觉化的呈现。相⽐实物拍摄,动画形态的创作与计算机艺术同为“平地起⾼楼”,另造一个世界。

《⽩⾊的⻢》
另一部动画短⽚的《局外⼈》中同样充斥着⼤量视觉媒介的混⽤。
这部真⼈定格动画⾥,处于底层的打⼯者正是通过家中墙上的照⽚镜照自己身体/身份改造的变化,也是通过张望改造⼯⼚⾥电子屏幕中的AI来张望自己的梦想;在这样一个⾼科技未来感的作品中,“打⼯⼈”的主题和⼯⼚社会的布景乃⾄⽚尾的⽼派的THEEND字幕卡⼜不禁令⼈联想到早期电影默⽚《⼤都会》。

《局外⼈》
此次放映的影⽚,一⽅⾯因多媒体的形式践⾏着对电影媒介语⾔的超越,另一⽅⾯⼜让我们重新注意到这些影像与传统电影的关系,进而再度思考“电影是什么”。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叙事的影像段落有意⽆意地勾连出许多令⼈熟悉的影⽚段落,甚或需要在类型电影的视觉景观和⽂化符码基础上去再⽣新的影像及意义。
例如《⽂森特》这部短⽚,创作者乐毅就不讳⾔受到⾹港⿊帮⽚的影响,而所谓赛博朋克的九⻰城寨景象我们早已在《银翼杀⼿》中领略过。当创作者来到现实中⾹港,其感知视⻆却更多地是受虚构作品《银翼杀⼿》中⽣成的经验与⽂化想象的影响。

《⽂森特》
《月球旅⾏记》这部早期电影代表的⽚段也数度出现在了短⽚《丢失的未来》中。影⽚梳理展示了过去18~20世纪的⼈们对于新千年建筑、科技、城市规划、⽣活⽅式等的构想蓝图,影⽚的趣味正在于观众将之与影⽚外自己所处的现实/现在的时空做对照。

《丢失的未来》
影⽚当中出现了一个⿐⾏怪,据创作者介绍,这是德国⽣物作家幻想出的动物,并最终将会因核灭绝。动画创作如何处理这一虚构中之虚构、过去中之未来或未来中之过去的事物质感,正体现了创作者对于时空关系的理解。⿐⾏怪的视觉呈现是一个典型,它虽然是未来之物,但样貌却更像史前的古⽣物。
联系《卫塞节》《⽂森特》等⽚同样随处可⻅的传统(如佛像)与时尚(⽆⼈机等科技产品)的杂处、混淆及相互颠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影像特别是沉浸式影像的⼤量传播与触⼿可及,现代⼈对于时空的感知也在发⽣变化,不仅时间是⾮线性的,时空间的边界也在消除,正如⼈们在掌中可以自由切换的界⾯。
此次⼊选的作品中,即使是叙事更为常规但也极其精彩的剧情短⽚如《漂流》《台⻛来之前》,同样也是⾮常灵巧地在记忆、梦境与现实的场景中往来穿梭。

《台⻛来之前》
以鲍德⾥亚“拟像”概念所命名的短⽚《SIMULACRA》更是以极具冲击⼒的形式引⼈思考新媒体发展中虚拟与真实及⽂化主体性的问题。
短⽚融⼊了舞蹈、能剧,在新⽣⼉的啼哭声中,年⽼⾊衰的艺伎分裂出⻄⽅⾯孔的舞者,布景时而是⼈⼯化的舞台,时而是旷野,时而是抽象的书法字符。

《SIMULACRA》
不同媒介语⾔体系的符号究竟拼凑传达出怎样的感受和意义?创作者将问题放置在观者的经验与影像之间,⼈们可以对视觉符号做出⽆限多的阐释。⽽影像也并⾮是已完成的作品,影⽚作者在”拟像“这一命题下,从理论-装置艺术再到短⽚不断叠加,从理性到直觉,真正的作品其实是其⽣成的动态过程。
在采访中,创作者表示自己逐渐意识到了身处在共享构建的开源代码中,抄袭和挪⽤随处可⻅。既如此,“哪个世界更真实?”,以及,不同概念的边界⼜在何处?
新的媒介体验正悄然改变着⼈们的认知,年轻世辈⽐从前更加渴望边界的消除、意识的流动,但现实中的秩序做的可能是反作⽤⼒的拉扯。
我们可以从《漂流》这样的作品中轻易辨识出一些社会议题符号,但这些穿插在影⽚中的符号性元素也并⾮是对海外想象的迎合。随处可⻅的议题性符号正成为我们的现实:我们是在⾼度符号化的词语中解读现实、确认同类的。
另一⽅⾯,即使退缩到个体的问题,社会议题的符号仍旧⽆孔不⼊。
尤其是《漂流》《秘密基地》两⽚,尽管场景极其封闭狭⼩,叙事看似简单,但前者的身份认同与代际沟通、后者的语⾔隔阂都不可能悬空于集体的现实秩序之外——⼈们被困于各种身份符号与身份规训中,也正因如此,就格外渴望悬空。
《漂流》中,一个⽆法解决焦虑与困惑的男孩最⼤的乐趣是开一台⻋在夜空⾥打转佯装⻜⾏。想象,是这个男孩得以悬空的⽅式;⽽在《浮浮》⾥,曾经编外的、在野的捞⼫⼈最终上了岸,依循现实的逻辑,进⼊到一个可被辨识的⼯⼈身份中,做梦,也是他得以悬空的⽅式。
漂浪在海量的影像流中,新世代的创作者并没有在极致的形式中做情绪的自溺。从超现实的媒介语⾔再到短⽚放映的互动⽅式,他们以更灵巧的操作给现实以回荡。

《浮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