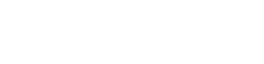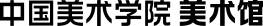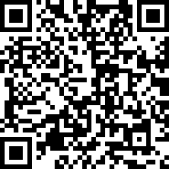2020跨媒体艺术节·韩岭展区开幕式

2020跨媒体艺术节·韩岭展区开幕式
素材来源:网络
“近未来”是即将到来的和正在到来的可能生活;这临近、迫近的未来依然存在无数“未知的未知数”。作为宏大宇宙中无比偶然的存在,我们必须用我们的智慧和想象去启动一个开放的、反命运的未来——谱写出那一首充满可能与潜能的未来之序曲,播种下属于我们这一纪人类的文明的种子。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高世名

2020跨媒体艺术节·韩岭展区开幕式
素材来源:刘益红
2020年10月31日晚,“近未来:可能生活”2020跨媒体艺术节在宁波东钱湖畔启幕。艺术频道此次直击艺术节现场,采访了9件作品背后的14位艺术家,与这些平均年龄25岁以下的青年创作者,讨论了他们对“近未来”的理解。
烟火行星
《史记·律书》:“鸣鸡吠狗,烟火万里。”描述的是一种人声鼎沸、鸡狗乱跑、炊烟袅袅的热闹市井生活景象,这是我们曾经的生活,也是我们记忆中的景象。在离我们曾经口中的“未来”越来越近时,我们回首昨日,那种人声喧嚣与人情冷暖也越发可贵。
在东钱湖畔,韩岭似乎就是我们暮然回首中的那个灯火阑珊处,白墙黑瓦石板。“烟火行星”是由30余位艺术家用自己手的温度来参与“现在”,不断地靠近“未来”。凝结于街道、河川中的诸多空间装置,锻链成浩瀚荒蛮宇宙中那条可瞬间幻游的悬置隧道。
潘子申
《种子舱》


潘子申:我们对“近未来”有许多科幻想象与向往,比如星际移民,我想把这种希望像种子一样保留,封存在如飞行器一样的容器里,穿梭到未来,把我们的希望带向遥远的时空。这个种子舱被放在这个巷子里,也是从平凡人家的烟火之气中,上升出一个对“近未来”生发希望的场域,新旧建筑之间出现了一个时空隧道,作品的整个设计都是为这个空间所制作的。

我的作品中会出现一种相对冰冷的机械,描述的是人类的器官被替换以后的现象。最后的希望可能是寄托在一个浓缩的意象当中,里面传达了人类经过多次反思后的结果。
这其实是我第一次尝试在户外展出一件作品,又是在一个以古建筑为主的老街环境中做,会有很多不受控的意外因素,但同时也会激发一些新的想法。为了保护传统街区的原始墙面,我选择搭建支架的方式呈现作品,形成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对比和美感。这既有一种人造物的构成感,又有置身民居自然状态的混搭感,我觉得很有趣。

/
石玩玩
《街角物语》


石玩玩:我的作品《街角物语》的英文名翻译过来其实是“白铁皮的爱情”。我采集了韩岭7个中年人的初恋秘密,然后把这些秘密转换成了摩斯电码,在街角闪烁。
说起“近未来”,我想象的是这样的生活:非常有烟火气,每个人都忙忙碌碌,有自己的生活和喜怒哀乐,但是抛去这些平庸的日常,还有一丝美好在一个偶尔的生活的角落和缝隙里。每个人都会憧憬自己的未来,它建立在过去的基础上,只有体认到这一点,我们才能够生发畅想。所以说当我在考量“近未来”的时候,我想先从过去开始谈起。

我觉得艺术到宁波韩岭这样的环境中,能带来一种崭新的视角。路过的大家能看到这些灯像星星一样在闪烁,即便可能不知道星星在说什么,其实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有这样的一种心情,勾连起这些故事。借此,观众也能联想到自己生活的状态。
我近几年的工作都基于在地创作,创作的环境还是要跟作品的内容有足够的关联度。我的作品跟这个地方、这片土地的关系是什么?它的情感联系是什么?我能给予到当地的环境和人群什么?我能跟他们沟通什么?我认为恰恰是艺术最需要关注的问题。所以我的这个作品到这个地方来讲述当地人的故事,它能和更广泛的观众群形成情感纽带,一种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
顾 楠
《捕梦网》

顾楠:在印第安的文化传统中,捕梦网常被挂在床头或门口,美好的梦境从网中心的空洞中进入梦乡把噩梦阻挡在境外。捕梦网通常是用丝线和皮革编织而成的,捕住的是个人的梦境,而我的捕梦网由钢铁制成,用于捕捉集体的梦境。
许多集体意识随着遗忘被埋入更深层的意识域中,只会偶尔在梦境中出现,在现代的城市中难觅踪迹。反而是多靠世代相传,或遗落于乡间,从意识的断口中流出。所谓“近未来”,可能就是在我们的意识地层之下。

DISEGNO 跨媒介巨构
主题“Disegno”来自吉奥尔格·瓦萨里的《名人传》。瓦萨里认为,自然(Nature)是绘画及雕塑的“母亲”,而诸种艺术的“父亲”则是Disegno。Disegno是一种力,创造的原力和巨力。媒介展演系以瓦萨里“DISEGNO”为名,以诺思洛普·弗莱“高山、花园、洞穴、熔炉”为构,20名三年级本科生对应巴勃罗·聂鲁达“二十首情诗”数列,通过20件作品向二十世纪的二十位艺术家致敬。而“一支绝望之歌”则通过一件作品致敬今年去世的贝尓纳·斯蒂格勒,并以此纪念整个二十世纪艺术史。

素材来源:王若兰 马原驰
高泓烨 欧杨心怡
《所有人反对所有人》

高泓烨 欧杨心怡:我们的作品灵感来源于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也许戈多他永远都不会来,但是他们还是在等待着。戈多这个意象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可能是上帝,可能是希望,也可能是死亡,每个人对戈多的见解都不一样。而我们创作的这个手的形态,则是引用了《创世纪》这幅名画里的元素——上帝在创造亚当时他们手部的动作,但我们没有完全复制这个动态造型,上帝在创造亚当时,两个手都是手背朝上的,而我们是一只手的手背朝上,另一只相反。

对于像韩岭老街这样的建筑空间,如何因地制宜地去改造、放置这样一件作品,如何在整个跨媒介巨构里处理 花园 这个独立空间并且撑满它,要让它符合整体基调不脱节,这些都是难题。整个展览空间,我们会有空间组来进行结构划分,将大家的作品连成一个整体。我的作品就相当于是巨构里的一个小零件,它服务于总体的叙事架构中。

素材来源:朱朝晖 等
我们认为,花园的空间定义是丰富的、鬼魅的,而且很多时候它是用来观赏用的,其含义也对应了戏剧史,戏剧的舞台是观看的窗口。我们设置了四个观看点位,前三个室内的是从不同的戏剧构图上观看,第四个则是进入花园身临其境地体验巨物压迫下的感受。当人们走进这个空间,近距离地去感受这件作品时,这个巨物的形式力量就会持续下去,不断地推进。我希望它能传达给观众或荒诞或震撼或感动的不同感受。
作品在白天与夜晚的不同灯光效果下,也能带来完全不同的感受。白天的自然光线下,由外往内观看,我们想凸显的是天空与手的关系。到了夜晚,我们根据设计的观看构图,对应地去打灯光,真的很希望观众在看作品时,能够发现我们设计的每一种构图。
意识圈
开放媒体系引用俄罗斯科学家、宇宙学者维尔纳茨基 Vladimir Vernadsky 与法国神学家、思想家德日进 Teilhard de Chardin 的“意识圈”理论来探讨人类在地质圈、生态圈之后进化而形成的巨大网络—意识圈,根据双子楼式的传统建筑空间设计成一场“意识之游”。展场以一个巨大的意识圈雕塑为轴心,57位艺术家的38件作品依空间划分为“生态、灵光、刺点、嬉弄、对视、书写、吊诡、消解、谐振”等九大主题区块,环绕扩散并共构出庞大的意识网络。
陈 欣
《阿留邊畿夜宇和》

陈欣:作品的名字“阿留邊畿夜宇和”,这句话初看可能会感到有点不知所措,它写于日文假名草创尚未定型时的日本,是高僧明惠上人解释教义时使用表音汉字留下的语句,意为“如是(就应该是这样啊)”。当时日本在有语言、但是还没有文字的时候,他们用中文的汉字当做一个音读,来表达他们自己的语言。这句话其实就只是保留了音读,没有保留意思。这个跟我作品的表现形式相仿,也是保留字形,但把字本身的涵义给消解掉了,而这背后也隐含了一种流动的精神。
我的这段作品表现的是一台机器在思考汉字应该是什么样的,它在慢慢打印、修正自己。影像中出现的的汉字都是我用这个神经网络去生成的伪汉字,这些在架空历史想象下聚合的伪汉字符,昭示着汉字字形在意义消解后的的流淌和迭代,同时表达的是一种对汉字传统话语权的对抗。我认为汉字是不断流动、推演的,字的背后其实是一种造字的精神。

当我想到“近未来”这个概念,我会想到对于未来的一种假想,而我在作品中所虚构的场所就是以假想去反映现实问题。在这个未来里,“误差函数”成为了这台机器正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其实我有观察它,我让它学习了200遍,但在这之后,我观察到它的这个误差并不是一直在降低的。就好像我在刻一个字一样,有的时候刻坏了,或者说把要的地方给刻掉了,我就会再次把它打乱,让它回到比较无序的一个状态,然后再继续刻它。
误差函数也是这样的,在跟真正的汉字的误差接近到一个值的时候,它发现没有办法继续前进,就会打乱自身,再从一个相对比较无序的状态回到一个相对有序的状态。
/
吴元安&杨思韬
《平行圈》


吴元安:我的作品是一件尝试用光和声音进行创作的视听装置,我们用光在封闭的暗空间里做出各种形态和声音,我负责视觉激光运动编排以及空间展陈设计部分。
这次创作最初的概念是一个平行宇宙,讲述两个对称的镜面圆环空间相互运动、交织和对话。在这个平行圈中,光线和声音不断地流动变化。
我在其中介入了 Anthony McCall 用激光做空间雕塑的方式并加入了自己的创作构想,比如:镜面的对称以及宇宙的概念。这和我以往关于“近未来”主题的科幻创作都是一贯相连的。
/
刘炜彬 王嘉辉 申一涵
《祝旅途漫长》


素材来源:王嘉辉
王嘉辉:这件作品是我们Surfing the Surface小组对疫情做出思考之后的具象化呈现,我们起初思考的是作为艺术工作人员该怎么面对疫情之后的困境,接着用了VR的形式试图将我们在后疫情时代的状态展现出来。
作品提供VR内部与外部两种观看视角。VR之内是五个人的故事,从个体角度出发去体验和适应全新的状况。VR之外则借观众的观看作为参与虚构了对话的外在表现形式,内外交织,共同构成于大事件之后个人的困顿与对真实的追寻。

我们的作品中并不提出任何具体的解决方案,因为对于巨大且庞杂的未知性,我们也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我们是以个体的姿态置身其中。其中的那个庞大的黄色球状物象征着无声无息却又扑面而来、没法忽略但又不得不去面对的困境,我没有给它具体的解释。
而作品标题《祝旅途漫长》其实也是我们对个人困境的态度。当面对突如其来的当下,我们要一直处于开放的状态去接纳“近未来”,VR里的场景也是在创作的过程中慢慢推演出来的。

/
余阳丰 李韵婵
《南方高速》

余阳丰 李韵婵:《南方高速》以无厘头影像的方式呈现了一场荒谬的高速公路堵车。这几年愈发觉得社会发展的迅速,在这个过程中存在很多“魔幻景象”,基于此衍生了这个作品《南方高速》,同时也是致敬科塔萨尔的一部小说,其中描述了一个抽象的堵车事件。
我们想对这个现象提出质问——原本应该节省时间的高速为什么堵车呢?整个作品用到日常中很多常见元素,包括一些视觉上比较冲击、夸张化的呈现方式,同时也介入了网络文学的构架,这些从内容上来看跟现在大部分人的生活其实是很接轨的。在堵车过程中,各种难以验证真实性的信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在高速的资本发展过程中,个体的矛盾日益明显。
我们其实还想抛给观众一些问题:当人漫长地被困在的狭小居所,通过互联网设备这个唯一的、连接真实与虚拟的介质,是否能通过这扇光怪陆离的景观社会窗口看到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寻常?
虫洞日志
“虫洞”与其说是一种假设,不如讲是一种信仰——在浩瀚荒蛮的宇宙中存在着一条可做瞬间时空旅行的隧道。科学家们前赴后继渴望证明他的存在,幻想家却早已将它作为了灵魂安置的彼岸,企盼着未来有无数可能,逃出被决定的桎梏,就像影像的跳切,分割却碰撞出自由的律动。实验艺术系构筑的“虫洞日志”期翼将人类粘合成一种新的想象共同体,40余件作品在传统建筑群中构筑着一场波澜壮阔的星际之旅,观众藉此成为时空旅人,从黑洞到白洞,寻找并踏定未来历史坐标。

素材来源:谢雯

范献鑫 《Albedo》

徐健 《数据主义·Dataism》

陈勤 《异化云》
张 听
《充满欲望的人》


张听:这件作品的想法来源是我对近年娱乐行业的思考。看肥皂剧、明星八卦、综艺已成为当下人们在平日里“自我麻醉”的一种方式,人们在消遣娱乐的过程中逐渐丧失思考能力,让自我扁平窄化。久而久之,低刺激阈值的东西就会让人觉得索然无味。
这次的影像作品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空间,我用粉色的灯管和一些装置作品进行布置,尤其是看影像用的坐垫换成了拜佛的莲花垫,它多了一种拜佛的意向,可以拜也可以坐,拜向这个作品的时候,就像是拜向欲望、拜向物质。
宁波韩岭这个地方的古建筑和我们的作品会有一种冲突的意味,这很有意思。人流熙熙攘攘,凑热闹的与看展的人都会让我觉得有趣。

素材来源:张听
“近未来”,是主动塑造未来的勇气,也是联通现在和过去的可能。在2020跨媒体艺术节,青年艺术家们通过与“近未来”的对话,向未来发出邀约。
展览将持续到11月10日,在此期间向公众免费开放。欢迎更多观众来宁波东钱湖畔,找到自己对“近未来”的解答。
2020跨媒体艺术节
展览时间
2020年10月31日-2020年11月10日
展览地点
东钱湖韩岭 / 东钱湖教育论坛张永和建筑艺术展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