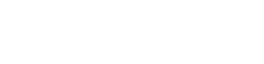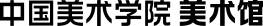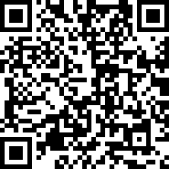艺术频道 NO. 11

第77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VR单元全球官方展映·中国站于9月2日-12日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举办。本次展映是威尼斯国际电影节VR单元在中国的首次落地。观众可以在本次VR展映中体验到全球最新的VR/AR/MR叙事及交互作品,感受虚拟时空带来的全新经验。中国美术学院和砂之盒沉浸影像展是此次威尼斯电影节VR单元的官方合作伙伴和中国站主办方。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艺术频道栏目组邀请到此次展映组织方的相关专家学者,围绕虚拟现实的技术、观念、未来走向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哲学命题展开讨论。

高世名:中国美术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
翟振明:广州大学R³技术研究所所长,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楼彦昕:砂之盒沉浸影像展创始人
宣学君: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网络与游戏系副主任、副教授,XR Lab负责人
高路:影视与动画艺术学院影视制作系讲师,XR Lab负责人
于朕:设计学院综合设计系副主任、讲师
俞同舟:创新设计学院讲师

高世名:他们这几位都是自己操作的,但是我们翟振明老师应该是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早来论述虚拟现实的哲学家。我们楼下在大厅开幕式的旁边墙上有一溜时间表,那是在1998年的时候,他的一本书里面做了一个未来时间表,从2000年到3500年。刚才我们在底下普遍认为慢,现在大家认为2500年基本上就已经到3500年的事了,因为技术的迭代和速度、加速度要比我们想象的快,所以说特别想请我们翟老师讲一下。

展览现场的时间表,引自翟振明教授《虚拟实在与自然实在的本体论对等性》一文
翟振明:这个概念时间表有个特点,它第一阶段讲VR,第二阶段段讲ER,就是Expanded reality。它就是VR+物联网的结合,VR和物联网现在是没走在一起的,搞物联网是物联网,搞VR是VR,到第二阶段它们就结合在一起,在VR里面操纵物联网里的所有设备,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用出来,就在虚拟世界中可以生存,不用出来,如果小朋友一出生戴上一个VR设备,他就不知道有这种现实世界,它就是对等的,本体论上的对等性,这就是我论证的内容。我还按照这个思路——技术的迭代写了一个时间表,我说这不是预言,而是技术迭代的逻辑。马斯克就是搞脑机融合的,我是坚决反对的。他(芯片)就直接插人脑,那有可能把人的自我意识给抹掉了,也看不出来,这很可怕的。如果没抹掉,其次这个危险就是外来的力量控制你,这也很危险的,所以马斯克让他对付病人还可以考虑,健康人的话绝对不能考虑。这个是伦理的最必要、最基础的原则。人是目的,不是手段。VR是目的,物联网是手段。人控制物。但是社会政治的力量,它的自然景象是物联网控制虚拟世界。所以我们如果没有使劲地以人本理性来先去堵它的话,我们人很有可能就变成物联网的奴隶。戴着VR被用来当物联网的界面,这是危险的。
于朕:很多刚才翟老师说的互联,包括脑机接口,我称之为“万脑互联”,所有的虚拟、所有的现实就全部都在大脑当中了。
高世名:这不就是《黑客帝国》吗?
俞同舟:我发现所有的问题不在于我们如何去区分什么是现实,什么是虚拟,反而是应该去考虑说,现在的虚拟和现实当中到底还存在多少不一样的维度,如何让我们作为一个肉体的人平滑地在当中生活,而不在于说对抗两个世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到底要去哪个地方。
高路:刚刚你讲到,你现在是通过VR设备来观影,那么我就可以从一个影视发展的角度简单地说一下。我们为什么现在永远习惯于矩形的这样画幅,这个只是一个阶段,因为人对自己感官的需求永远是不断地要去满足的,只不过这种矩形的画幅的方式存在了100多年,但是随着我们对它有更多的需要,也许这种视听的体验方式就会通过别的设备(实现),当设备足够成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闻到电影里的气味,我们可以跟电影里的场景发生交互,我们可以跟里面的演员进行对话,我们的对话会改变剧情的发展,你真正参与到叙事的过程中去,那么我觉得这就是VR它作为一个启迪,或者是作为一个切入的一把钥匙,它在影像上存在的一个意义。因为最早大家认为360度的视频就是VR,可能它只是其中的一种,但我认为真正的它是交互的一种叙事,交互的故事,一种影像。我们打破第4面墙可以钻到这个里面去,跟它产生互动。其实我们没必要在VR或者AR上纠结,因为为什么叫XR?X可以是Cross Reality,我穿越所有的这些形式,我也可以是Extended (Reality),就是扩展这些。
翟振明:我的概念是 Expanded (Reality) 。
高路:OK,那我们再加一个Expanded (Reality)。所以我们现在看AR或者VR,我们不要刻意把它区分开,对我来说我觉得这些技术是一把钥匙。这个钥匙是什么?它是打开我们现实世界和我们精神领域或者说是我们情感领域想要去介入的这样的一个世界,它提供了一个方式,也许以后会有更升级的方式,更科学、更有效的一个方式,它最终的方式是要把我们的现实世界跟这些我们所虚构出来的也好,或者说是去反映我们精神内心世界的这些世界,打通、混合,然后这个世界通过这些东西改造成一个综合性的、混合性的世界,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用刻意的去区分它的一个特定的概念,它都是过程。
楼彦昕:大家平时看手机,看电视、看电影,你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3D压回2D的内容,因为你实际上看到的是个平面内容,但是AR、VR技术第一次把3D的空间世界完全再用三维的方式还原给你,这是我们过去跟所有的信息交互的方式,原先都是二维化的,现在第一次变成三维化,跟信息进行真正三维化交互的时候,这个时间的节点和机会。因为这样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未来跟整个世界的交互的方式,不管是AR、VR,跟世界的交互方式、跟人的交互的方式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变化,是因为我们跟信息交互方式已经产生了本质上的变化。
宣学君:其实有个很好的参考对象就是电脑。电脑发展这么多年了,其实有一个东西,其实就是鼠标,鼠标就是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我们通过它去指挥电脑里面的东西,但是这么几十年来鼠标它没有消失,它还在那里。那么现在VR其实戴上手柄,这手柄其实就是多了个鼠标一样,就是我们其实多了个媒介。那么另外一点就像刚才接着上一个议题一样,如果我们要去真正体验,其实越少的负荷会越好,头盔就变成另外一个大的鼠标。其实我们现在都是通过一个媒介去体验,或者说想去获取一个新的体验,这个可能现在是比较直走的这么一个环节,我觉得以鼠标来解释可能是大多数人比较好理解的,其他的话我们也可以从产业去理解。因为第一轮的VR的风暴其实已经过去了,那一波没冲过去,所以对这个产业来说,它是蛮受伤的,它还要恢复一下,再来冲第二波。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刚才的话题的,为什么说我们看都会像游戏一样,是因为从我的角度来理解,是因为现在VR设备里面交互它是不可少的,但是这种交互性恰恰又是游戏,不管是几千年以前的游戏也好,现在电子游戏也好,或者一般年轻的游戏也好,游戏的特点其实就是交互性,那无非就是把这个线下的交互性最后落到了线上来。那么目前我们内容里面因为要变成三维,那么刚才楼彦昕说了,就三维扫描它其实存在很多的问题,也不是每个创作人都会去做的,那么现在就是说3A场景是最好实现的,也就3D建模,不管贴图也好,不管渲染也好,它呈现的东西他是动画的一种质感,动画的一种效果。无非就是说我们在看的时候,我们故事可能相对还是一个线性的叙事,但是我们在体验的一些环节里面,我们可能会有一些非线性的东西。当然从交互叙事现在包括影视剧也好,这个游戏也好,包括动画也好,现在开始有一些非线性的叙事的产品出来,虽然量不多,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尝试。虽然东西出来,但是它整体来说每个环节它还是线性的,无非交互环节变成非线性的。
楼彦昕:我以前一直觉得VR是一种连接,但后来我发现它其实并不是一种连接,在我们过去的这几年的探索,包括自己做作品,包括看别人的作品,发现其实它是一种通用型的基础设施。它会变成说跟不同的媒介结合在一起产生新的变化。如果大家就今年这次有看过一次VR电影的作品,包括还有线上的版本,他就会发现其实这里面会有VR的游戏,有VR的纯粹艺术表达的作品,然后有VR戏剧类的东西,然后VR靠近电影,所以它跟传统——尤其是我们前两天做工作坊(对比来看),就会发现说一个系列团队,他运用这项工具,这个技术它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会靠近剧场一些;如果说是(做)电影的人,他用这样东西做出来可能会更靠近电影一些,所以实际上我觉得它是传统媒介的一种催化性的一个原料,就它跟传统媒介的形态甚至说跟传统媒介的人去结合产生出来的东西是一种混合体。我们没有办法,我觉得现在从我的角度来讲,并不会认为说要它就是一个单一的媒介形态,而是它是一个光谱,然后它在每个颜色色域里面都有自己相应可以找到的类型和内容。所以我相信肯定有一些内容可能他会更靠近游戏一些,但也并不是所有互动类的内容都叫游戏,所以我们现在叫VR,都管这个通用概念叫做体验,叫VR体验,它也不是VR游戏,也不是VR影视。但是如果它基于玩法,就它以玩法作为核心的话,它可能就是靠近游戏,它属于游戏。如果它是基于表演、演出,可能它就是比较戏剧,所以我觉得VR还是一个可以跟各种媒介去结合的一个通用型的工具框架,或者是技术框架,然后基于跟这个技术框架去结合会产生新的媒介的表现方式。
宣学军:我们很大的目的,就是希望把这些作品带给大众或带给更多的人,因为我觉得如果去做创作,你没有体验过、没有看过,其实什么东西都是空谈。包括大众现在对VR的理解都是想象中的,不是基于真实体验以后的。怎么让大众理解?我觉得我们搞这个节就希望大众对此有更多的理解。
高世名:其实大家都聊得挺多的,我其实想问一个问题,你们觉得今天的VR,我们有时候其实很难去判断VR作品它是一个电影,虽然我们用了VR电影的说法,因为一个根本问题是叙事的问题,这些在VR电影的意义上来说,你们觉得现在有哪些技术的瓶颈?这个其实大家可以来谈一谈。然后还有一点,现在的情况,VR作品往往太像游戏,这样一种观点的经验,这之间有巨大的差异。那么当我们赢得交互性、参与感的时候,我们失掉的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它是什么。任何一个新东西出来之后,其实我好像增加了一种体验,我们都会丢掉另外一种体验。其实VR的虚拟现实从它最原始、最朴素的意义上,它是很古老的。我们以前讲聊斋里面讲那个故事是吧,看到一幅壁画,看到壁画里面场景栩栩如生,看着我看进去了,看进去之后在里面爱恨情仇一番,然后最后出来最后原来才是一瞬,是吧?这就是一次虚拟现实的体验。同样我们看一幅古典绘画,欧洲的古典绘画,我们去看的时候,好像阿尔贝蒂说是一个窗口,好像看这幅画,好像通过窗口看出去的世界,我们把图像看成世界,这就是虚拟现实的体验。我们说山水画是卧游,是吧?“欲令众山皆响”,这也是虚拟现实体验,这就是最朴素的意义上的虚拟现实。所以我说其实这是艺术的一个基本的构造,就是说它是通过制像行为构造出了另外一个空间,一个类世界,让我们可以超拔出我们此刻的现实。
2000年我当时到伦敦,伦敦的泰特现代馆开馆,开馆展的时候,除了它很牛的陈列之外,它还有一个专题展览,叫做"Between Cinema and a Hard Place"。那么今天实际上我们会发现VR和AR是Cinema和Hard Place同时兼有,所以我们讲我们实际上并不会真正的像黑客帝国那样沉浸在Matrix里面而遗忘现实,我们始终只有一个现实,就是混合现实,交互的、混合的现实,我们一会儿进去,一会儿出来,或者说我们同时既感受到此刻的这个现实,又能够看到那个现实,这个是我们现在的一个常态,当然这个常态会维持多久还不知道。未来,我在这方面技术方面略有悲观,我觉得这个黑客帝国就是未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甚至觉得翟老师的3500年的时间表,实际上它要提前1000年时间,可能到2500年或者说至少2800年,可能那个时候就已经处在那个状态里面。
我刚才在讲的前两年,我给我策展专业命题的时候,开头就是未来某个世纪,赛博旅行成为常态,一伙人正好邂逅了一片墓地,非常浩瀚的100多亿人类的墓地,网络第一代的墓地,那就是在你的3100年之后,就是人类文明成为史前史之后,那个时候开始出现的第一次觉醒,突然发现有一片网络一代的赛博墓地,到底是什么?这里记录着无数人,像我们这种生活的、两个现实中的这些人的史前生活,这种史前生命,然后开始产生考古,然后开始产生催生反叛的意识,开始从 Matrix里面开始叛逃,是吧?开始出现各种东西,但是不要忘记的是,当我们看到《黑客帝国3》的时候,我们发现连尼奥本身都是又一重Matrix的病毒而已,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功能性的设置,它也是一个程序。那个史密斯先生是一个杀毒软件,它其实是这样一种关系。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会发现现实的一重又一重,最后形成了一个无限的循环。那么最后,我也常常在想像,万一这一切都实现,那么它最终有没有主人?有没有控制者?那个Master。是吧?如果只有最终极的Master,它好像必须是在Matrix之外的对吧?也就是它是在世界之外的,只有这一个个体、这个主体在世界之外,那么它到底是主人还是奴隶?
翟振明: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外边呢……
高世名:第一,我们无法判断他是主人还是奴隶,因为他在为整个系统服务。其实Matrix中的人倒是很幸福的,在里面爱恨情仇了,然后他们有他们的人生,但是看起来像神的人,实际上他成为维持这个系统的唯一的劳工。然后第二呢,就像翟老师说的,他自己也会产生疑问。对,他会不确定。就像我们修巴比伦通天塔,修着修着修到无限的时候,突然之间产生争议,我们到底是在往上还是往下?我们到底是在往什么方向走,那个时候会产生一场叛乱,这也是巴别塔没有修成的原因。不是因为语言,而是因为分不清上下,分不清方向。同样的,未来的Matrix的施动者、驱动者,他也无法判断自己是在之内还是之外,是不是又一重幻象……
翟振明:不是一个驱动者,是一群技术官僚就是驱动者。
高世名:但是最终按照逻辑,他们最终会合并成最后那唯一的一个。
翟振明:没有,一群人被人理解成一个人。(笑)
高世名:那就是现实嘛。
高世名:我有两个想法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我曾经问过他们几位,我说在什么意义上这些VR被称作电影?就有点像是一个新人穿了旧衣服,穿了旧鞋子,我指的是VR电影这个说法。在我的期待和理解中,我觉得VR它不应该往电影这个19世纪发生的那个街区发展,而应该,VR就是构造世界,就是构造小世界,就是构造出不同的视觉,不同的逻辑,甚至是不同的规则。所以说在这里面,艺术家的根本就是创造世界,创造一个新的小世界,在这个意义上才有那么古老的中世纪的隐喻,说艺术家是第二个上帝创造出第二个自然。所以这个意义上,我觉得VR是它作为一个技术,使我们更有可能创造一个沉浸式的、一个可体验的世界,这是第一点。那么这个世界,它并不是说让我们去脱离现实、沉浸其中的那个梦想——做梦。如果有太多的这种梦,它其实某种意义上就是软毒品,我们说就是精神鸦片。我好多年之前看过一个,应该是在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读过一本书,当时觉得简直是宝贝,叫《心我论》。翟老师知不知道?“心我”,“心”就是“心灵”的“心”,“我”就是“自我”的“我”,《心我论》,一个科学家和一个哲学家写的,它里面谈的全是那种“钵中之脑”之类的这种,因这些哲学命题以及科学幻想所产生的各种各样的伦理困境和悖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关于人在对自己梦想的沉浸所产生的那种功能的退化,这个功能退化是包括你的主体性的退化,你的意志的退化,这些东西。然后后来又看了一部电影,那部电影叫《世纪末癔症》。《世纪末癔症》里面讲的其实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软毒品,你通过戴上头盔,戴上你的整个这套可穿戴设备,你体验到翟老师上星期最爽的一次体验,当然这个最理想的会是我可以去做文旅,我可以去看故宫,我就直接……他去一趟故宫,我录下来就行了,我们就都可以去故宫了……这里面产生各种各样的情感和感觉的一种混搭和创造。这个已经接近艺术,就是感性的发明、感觉的发明,在你的狂喜之中加上一丝绝望,这是一种感性的发明。
当年我们99年做“后感性”(展览)的时候,我就一直想做这个事,我觉得什么叫“后感性”,我们正常的喜怒哀乐、七情六欲,这都是感性,真正的后感性是发明出我们不同的情感。比如说我们把忧郁这个事情,我们拓展成2000种,那么这就是艺术家对人性的贡献。我们一般来说高兴不高兴,然后只有有点小文人情调的,才会知道感伤和伤感是不同的,忧郁和抑郁是不同的,那么我们的情感就开始细分,我们的感觉开始细分。但是如果要我们在未来通过精算,通过你说的超人工智能、强人工智能……它的颗粒会变得更细,在这种情况下,人会慢慢地发生改变,人性会慢慢地发生改变,人道会慢慢地改变,伦理会改变。所以说这个就是技术所带来的一个大的发展,我想用16个字,我觉得大致可以概括我们翟老师20多年前的那个时间表,VR技术,就这一类混合现实技术的第一步,刚才讲过的“身临其境”,对吧?目前来说连这一步都还没做到,因为身临其境你会发现VR的大量的依赖于动画3D建模图像等等,它没有到达让你就说是真正的沉浸进去忘掉的程度,三体里面讲到的游戏也远远没达到,对吧?第一步“身临其境”,第二步就是“感同身受”。你的人工皮肤,所有的触点,感同身受,当然这个感同身受可以通过外部,从我们的神经末梢做起,也可以直接植入到人脑接口,直接从神经中枢开始给你构造现实,这是第二个阶段,就是从"身临其境"到"感同身受"。第三步,当你真正感同身受,而且一旦VR技术开始产生了就像他说的亿万人脑部相连之后,那就是“颠倒梦想”。第三步就是“颠倒梦想”,你不知道真还是假,不知道自己在哪一重世界里面,不知道我是在他的幻觉里面,还是我构造了我们的这些幻觉,也有可能我们是他做梦梦出来的一个东西。庄周梦蝶,而且这个时候你要知道有100亿个庄周,那个时候产生的一种就是一个超级重叠的平行宇宙,这里面一旦连机应该会不得了的恐怖,这是第三步,颠倒梦想。这个之后我其实一个相对积极的,我刚才说我比较悲观,但是一个相对积极的理解,就是说最后一步是破茧化蝶。破茧化蝶,我不知道是悲观还是乐观,由茧化蝶,就是我们成为新人类,那个时候就是真正地成为另外一种存在。“量子力学。”(翟振明)它可能真的跟我们今天不一样,我们同时生活在多重宇宙之中,同时生活在多重的世界里面。这个是我觉得16个字:“身临其境,感同身受,颠倒梦想,破茧化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