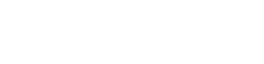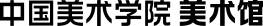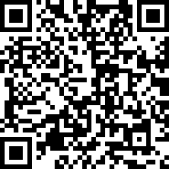3月8日,“纪念徐坚白先生诞辰100周年:白雪相和——徐坚白 谭雪生作品展”在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开幕。展览分为四个部分,一楼圆厅展出前三个部分:“艺苑继薪”、“桃李不言”、“晚霞满天”;一楼方厅展出第四部分:“白雪相和”。共展出徐坚白与谭雪生先生的创作共计近百件,展现二位艺坛伉俪的艺术创作成就、对于美术教育的贡献和相濡以沫的艺术历程。展览正在进行中,展期至3月31日。本期推送为徐坚白先生早年求学回忆视频,另附策展人张素琪于《浙江日报》发表的策展手记《白雪相和》。

“白雪相和”,是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近日展出的“纪念徐坚白先生诞辰100周年”展览主题名称。开幕式特地定在3月8日国际劳动妇女节。当天现场的女士们都收到了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朵玫瑰,插在以徐坚白油画《红玫瑰》为元素制作的卡包里。


徐坚白是20世纪中国美术史上寥寥可数的有成就的女油画家之一。谭雪生是她的终身伴侣,二人同出国立艺专(现中国美术学院)林风眠画室。林风眠曾担任艺专杭州时期校长10年之久,徐坚白又祖籍杭州,幼时曾在杭州随祖母读书,于是杭州,就成为夫妻二人一辈子念兹在兹之处。
“白雪相和”象征着二位先生相濡以沫的艺术人生,亦象征着他们的作品如雪般纯净、如磐石般坚韧的美学品格,是艺术与人生的交响。

开幕式上,徐坚白先生女儿谭加东女士一番关于父母对国立艺专、对故乡杭州的回忆,更是将现场带入了一种温暖的氛围里,听者无不动容。

我有幸全程参与了展览的策划和实施。我和徐坚白、谭雪生二位先生的缘分,始于2003年10月。此前两年,因为筹备刚落成的学校美术馆新馆开馆展以庆祝75周年校庆,杨桦林馆长陆续赴全国各地拜访学校老校友,征集藏品和校史文献。我作为助手跟随,见过吴冠中、王朝闻、罗工柳、彦涵、苏天赐、乌密风诸多如雷贯耳的老先生。
我们去广州美院寻访老校友的那次,恰逢徐先生谭先生在美国,没有遇见。10月初展览开幕在即,谭先生来电,告知我们他在广州,即将搭火车来杭专程送画,但因年事已高(先生彼时已82岁),希望有人去站台接他。杨老师遂派我去接谭先生。
之前我并没有见过谭先生。作为一个还在读研的学生,只能惴惴不安地在站台上等着,胡思乱想着见到这位前前前辈该说些什么。车到了站,一位老先生背着一个包、挎着一个长长的画筒下了车,不用说一定是谭先生了。画筒里装着的,是徐先生和谭先生的两件代表作品,为了赶时间、方便运输,他们把油画从画框上拆下来卷起来,由谭先生亲自背来。

此次展览中展出了这两件作品,加东老师说,原来这两幅画在你们这里!我说是啊,谭先生不记得了么,他亲自背来的,我们也有捐赠证书给他的呢。加东老师笑言,因为这两幅是他们珍爱的代表作,所以家里有留照片,但是两位先生面对照片怎么也想不起来这两幅画去哪儿了。可见当年在捐赠作品给母校时,他们也是拿出了压箱底的宝贝。
跟谭先生比起来,徐坚白先生于我而言只能算是“神交”——2003年谭先生来送画,她因为身体不好没有一同前来,后来也没有见面的机缘。原先我只是模糊地知道,她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油画家,是著名校友。对徐先生系统的了解,完全是借此次展览筹备的机缘,通过大量阅读她的手稿、评论家的文字,观摩她的作品,倾听加东老师的讲述慢慢建立起来的。在我的认知里,她外表娇小、内心强大,在人生的至关重要时刻,她总是能清楚地决定自己前进的方向并坚定地走下去。

徐先生出生于书香世家,是明代开国功臣徐达的后代。幼时曾随祖母在杭州生活,在南山路小学读过书。北大毕业的父亲曾安排家庭教师教她书画,因此她的旧学功底是极好的,这从展览中她的手稿一手娟秀的笔迹也可看得出。1941年,徐先生16岁时,投考进入西迁至重庆办学的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中国美术学院前身),在进行基础课学习之后选择西画系的林风眠画室继续深造。

林风眠和他的助教赵无极时常谈起学校的杭州往事,徐坚白没有经历过杭州时期,只是听听便很向往。想来这不仅是对老师和学长的一种天然崇拜,也是暗含了对于故乡的怀念。
谭雪生那会已经是她的男朋友,和林先生是广东老乡,自然也是非常亲近。两位跟随林先生学习时间并不长,却一辈子以林先生为榜样,终生记挂老师,以自己是杭州艺专的毕业生为荣。
此次展览中第一件展品是徐先生作于1944年的一件油画《自画像》,莫迪里阿尼式的拉长的线条,画出一位清冷美丽的少女模样。这件作品是徐先生保留下来的唯一一件学生时期的油画习作,它随着先生从中国到美国,从美国回到中国,又经历时代的各种运动,存世80余年,品相仍然非常完整。加东老师说,徐先生读书时自画像不止这一件,但因为这件是受到老师林风眠和赵无极高度肯定的,所以她特别珍视,再艰难的旅途,都呵护备至。

《自画像》的对面,展出的另一件油画《林风眠先生》,是徐坚白1999年为林风眠故居而作。当年是林风眠先生诞辰100周年,杭州市将故居回收,整理成纪念馆对公众开放。这件作品后长期陈列于故居的入口处,让参观者第一时间感受到林先生的音容笑貌。出于保护作品的考虑,目前故居展出的是此件作品的复制件。展厅里,年轻的学子和慈祥的老师面对面,宛如回到那个师生相拥于火炉前谈人生、谈艺术的现场。

优渥的家庭条件为徐坚白提供了进一步深造的可能。1947年,她远渡重洋,开启了在美国的留学生涯。从留学时期的照片可以感受到徐坚白那时的陶然。然而,当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来,对于新社会的向往,让她在收到男朋友谭雪生的信件后,毫不犹豫放弃了即将到手的学位,和有着同样理想的留学生们一起踏上回国的轮船。脱下旗袍大衣,换上制服,和爱人一起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全情投入。

徐坚白这样一位杭州姑娘,从此在广州安了家,创作的主题,也聚焦到广东一带常见的渔民。她认为,渔民是大自然生活的强者,他们的豪放性格、粗犷形象以及不论男女老幼都有的鲜明特色,海、船、鱼、生活,她都热爱去表现。她创作于1964年的代表作《旧居前的留念》,是新中国美术史上一件名作。饱经沧桑的三代渔家人,在曾经的船屋前合影留念,远景是一排排新居和欢欣的人们,新旧社会的巨大转变通过一张小小的合影,生动地展现出来。女油画家细腻的观察和表现,让这件主题创作具有一种格外的温暖。

徐坚白曾说,我爱,我有激情,我才画。也不止一位评论家说过,在徐坚白的色彩世界里,看到一位女艺术家的坚守,还有一些任性。整理展览文献和作品的时候,我常常在想,作为一名女性,在20世纪的中国美术界取得公认的成就,这条道路并不好走。那么,徐坚白先生“任性”的底气从哪里来?
除了原生家庭给她的丰富的精神和物质基础,使她从小能够自信、独立地成长,还有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先生谭雪生的支持、理解和包容。
展厅里展出了一份文献,是徐坚白简历的手写稿,而特别的是,这份手写稿的整理人,是谭雪生。徐坚白的学生李默回忆,2011年谭先生逝世后,徐先生对他说,不知道以后怎么办,没有办法再画油画了,原因是她结婚后,从来没有刮过油画盘子,没有洗过笔,都是谭老师代劳的。从这两个细节,可以深深感受到,谭雪生对于伴侣的爱护和包容,他承担了细碎的杂务,只让她安心作画。真正是现代版的举案齐眉了。

展廊里的年表,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从意气风发的青年,到踟蹰相扶远去的背影,一帧帧照片细数着他们相伴70余年的人生历程。
西子湖畔走出的女孩,以自信和从容面对时代的洪流,以家人作为强大的后盾,坚守艺术初心,以对艺术无比的热爱抵抗岁月的漫长,最终成为新中国艺术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存在。